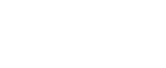《肆拾贰炮》之“二蛋”
《肆拾贰炮》之“二蛋”
——烨 雯
前 言:
莫言获得了2012年“诺文”后,全国的文艺界沸腾了,所有的媒体、电视、电台、网络和社会无处不在议论着、探讨着。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自己也属于一个文艺爱好者,属于一个有想法的文艺青年,所以早就想着拜读一下他的大作,苦于一直没时间,直到前一段时间,我终于买了一本他的代表作《肆拾壹炮》,看完之后我突然想到了我们村里的一个老光棍——“二蛋”。就好像莫言在《肆拾壹炮》中所说的“大和尚,我们那里把喜欢吹牛,撒谎的孩子叫炮孩子,但我对您说的,句句都是实话。”于是我就提笔写下了关于我们村里“二蛋”的故事,仅此而已!
……………………………………………………………………………..
“二蛋”说他要把家里的老房子装修一下,最主要的是把原先的房顶掀了,重新打水泥顶,然后吊一下顶,听他说的意思,好像是现在的铝扣板的那种,他还说要买一套四联组合柜……,说到这里在场的人都笑了,问他是不是要准备娶媳妇了,还有人说你就“炮吧”……
“二蛋”是我们村的一个单身的老光棍,小的时候就听村里人一直叫他二蛋,其实他是有大名的,至于叫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也从来没有问过,似乎在和我同龄人的眼中,“二蛋”就是他的大名,而他也确实就叫“二蛋”。说他是一个老光棍有点不确切,他其实只是一个光棍而已,年龄不是很大,虽然我不知道他的实际年龄,但我知道他真的不是那么的老,因为他和我爹是小学同学,或许是常年的劳作和岁月的无情,他的头发和胡须已经花白了许多,身体也佝偻了许多,这就是他给人的第一个印象。
我们村是一个坐落在太行山支脉中的一个小山村,世世代代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简单又朴素的生活,在群山的环抱中就好像一个“世外桃源”一样,纯朴的大山、纯朴的村民、纯朴地过着繁衍生息的简单生活,小时候我时常面对四面的环山想过许多问题,比如说“我们的祖先为什么会选择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定居”“第一个走出大山的人又是谁呢”,当然所有的疑问根本得不到一个确切的答案。听大人说村里什么时候修的路,什么时候通的电,有时候我已经不去考究这所有的一切了,改革的春风吹遍了神舟大地,中国大地发生着很大的变化,沐浴着改革的春风,我们这一代人应该说是最幸运的,对于生长在大山中的孩子来说,要想走出大山上学似乎成了一个不可取代的唯一途径,万千的学子挤身独木桥的时候,我没有被挤到河里去,回头望望,真的可以用“不堪回首”这个词来形容,我写过的一首短诗《山里的孩子》中曾经这样描述了走出大山的山里孩子的现实状态。
“我是一个山里的孩子/光着屁股长到了十八岁/终于有一天/穿上裤子/走进了城里/可谁知引来了一阵阵讥语/我用鄙视的眼光/给了他们一个对视/或许他们不明白其中的含义/亦或他们仍在寻找/那条属于自己的裤子”。
在宣泄充斥、物欲横流的城市生活久了,身心的疲惫把我们折磨的体无完肤,生活的间隙偶尔回到生我养我的小山村小住几日,也是一种享受,享受着乡村劳作生活的简单和家人在一起的舒心惬意。
正如别人说的,人的身体的确是一个懒惰的东西,在经意与不经意之间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体力劳动逐渐减少的情况下,我们的身体也就逐渐的失去了原有的“战斗力”,好久不下地干活了,偶尔下地干点活还真有点吃不消,那天下午从地里干活回家后还像以前一样和爸妈坐在门前的老槐树下休息乘凉,闲聊一些家常,和邻居聊一聊一年的收成以及应该在哪块地里种哪些作物比较合适,金秋时节的山村一切都是那样的别样,漫山的柿子树上挂着累累硕果,金黄的谷穗随都低沉着头,似乎顺着谷杆爬上的一只小小的蚂蚁都能让他趴到在地上一样,玉米棒子个个都是那样的饱满,这一切都给辛苦了一年的农人带来了无比的喜悦。
昏黄的太阳一步一步地顺着山角滑落了下去,仿佛给大山披上了一道霞光,映红了安静而祥和的小山村,映红了辛勤劳作一年的村民的脸,看着他们三三两两肩上扛着农具、柴火回家的身影,听着他们谈笑风生、聊着家常和收成,心里的那种久违的亲切感真的是久违了。这时候我点燃了一支烟,看着打火机的火苗在火红的夕阳映射下把烟点燃,一片青烟缭绕着袅袅上升,然后又逐渐的消失在空中。我的思绪仿佛又回到了小时候在家上学的时候,记得小时候放学以后或者是星期天总是和弟弟一起去地里挽猪草、拾干柴、上山上逮蝎子以及在母亲的带领下去挖药材。这样的话可以给家里带来一笔不小的收入,让原本不太宽裕的家可以减少一些生活压力,以至于到现在我还是会在每天在地里劳作的时候,自然与不自然间会去捡拾一些枯树的干枝,或许我是一个比较适合乡村生活的人吧,我一直是这么认为的。
故事从这里开始吧……
天边的昏黄渐渐的谈去了,天一点一点的黑了下来,母亲回家去准备晚饭了,我和父亲谈论着我的工作、今后的发展规划,还有他退休以后的生活构想。就在这时候从房后的街道上闪出了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身影,佝偻的身躯,略显苍白的头发和胡须是那样的参差不齐、杂乱无章,胡子和头发的花白程度基本上差不多,其实这不应该是一个像他那样年龄段的男人应有的形象。不过长期在农村劳作的人和城里人是没有可比性的,纵然他和我爸的年纪差不多,但他和比起来差距还是很大的,毕竟我把一直在单位上班,体力支出相对来说小的多的缘故吧。我从小就知道他是个光棍,至于他为什么一直没能够娶上媳妇,我真的不知道,也没有去问过,父亲应该是知道的,村里的大人们应该也全都知道,但我没从去专门去问过,至于他本人我更没有去问过,不是不问、也不是不敢问,是真的不忍心去问,因为在中国大地上,特别是在一个贫穷、落后、闭塞的小山村,一个男人如果一辈子不能够娶一房媳妇,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是一件特别难以接受的事,哪怕他们安于现状,表现的无所谓,我想在每个光混的心中永远都是一种无以言表的痛楚和人生中莫大的悲哀,或许他们的内心早已接受了一个人生活的现实、接受了无奈的人生。
还是和往常一样他和父亲打了声招呼,相互寒暄了几句,就在他准备转身离开的时候,父亲说:“二蛋过来抽根烟来”,他一边答应着一边走了过来,当他正面朝着我们走过来的时候,我发现了他的步履已经有了些许的蹒跚,甚至感觉走起路来有一种踉跄的感觉,他走路的时候两只手随着摇摆的身体前后甩动着,我真的想不到用什么语言去形容才是最恰当的,真的想不出,所以索性就不去想了,反正看起来挺滑稽的。或许常年的体力劳作已经快把他压到无法承受的地步了,不过我感觉体力劳作的支出毕竟是一方面,心里的压力和精神的长期缺失才是最主要的。他走过来之后我起身把我坐的板凳让给了他,然后为他递上了一支烟,本来他要从自己兜里掏打火机点烟的,在我得一再坚持下他接受了我帮他点烟,他一只手夹着烟,另一只手颤颤巍巍地环抱着打火机的火苗,就在我给他点烟的时候发现他的手背上全是褶子,就像秦岭的一道道沟和一道道坎一样,深沟里存在着沉积了多年的尘,已经被岁月熬成了想墨汁一样黑、想纹身一样无法洗去清晰可以的一条条深深的、盘延不断的岁月的痕迹。手心同样也是饱经沧桑,手指的茧子厚实而又黑黄黑黄的,甚至我看到了有几处裂口,裂口里的颜色与外面的颜色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把烟深深地吸了几口,烟雾在他的头顶缭绕着、从他杂乱的头发之间盘旋着缓缓的上升,最后彻底消失的无影无踪。
“二蛋,干啥去啊” 我爸问道:
“给我妈拿点药去,她这几天有点感冒了,在我姐家住着呢”。二蛋这样回答到:
说道这里不得不说一下他的母亲,他母亲具体名字我部知道,反正听村里人都叫她“白荣”,这应该是她的小名吧,她已经八十多岁快九十岁高龄了今年的过年的时候我还去给她磕头拜年了呢,当时我们只是看见她在床上躺着,或许她也意识到了我们的光临,只是嘴里支支吾吾的已经说不出话了,还记得前几年每年去拜年的时候她还招呼我们抽烟什么的。听人说她病的挺厉害的,没有几天的活头了,然而就在今年的正月十三她永远的闭上了眼睛,远离了一生的困难。听村里人说她也是一个受尽了苦难的女人,原先的时候是我们村“西坡脑”山上一个地主家的小妾,那时候的小妾就好比现在的保姆一样,洗衣、做饭、体力活都得干,还要经常受正房的欺凌,后来还生下来一个男孩,也就是我们村的“奶金”,在这里我们暂且不去说他,以后我会写到他的,还是继续“二蛋”的故事吧。新中国成立后地主阶级被打倒了,新中国实行“一夫一妻制”,她就被政府从火坑里给拉了出来,嫁给了我们村的“骡子”也就是“二蛋”他爹,嫁过来之后又生下了三男一女五个子女。女人的一生真是苦难的命啊,看着儿女们一个个成家立业,自立门户人也就渐渐的老了。一个即将九十岁高龄的老人如果死了也可以算得上是人生无憾了,但是她且还有“二蛋”这么一个长不大的孩子没有取上媳妇,我想她在死之前也不放心自己的这个没有成家的孩子……
当时我想如果有一天他的老娘真的走了,谁又去疼这个没有长大的孩子呢,纵然有兄弟姐妹几个送走他年迈的老娘是没有问题的,可是谁会想亲娘疼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疼她照顾他呢,毕竟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真正的家,我似乎看到了他的晚景凄凉。
一支烟已经抽完快一半的时候“二蛋”开口说话了,他和我爸说他想把和他大哥一个院的属于他的房子重新翻新一下,最主要的是把原先的房顶掀了,重新打水泥顶,因为已经年久失修,一道下雨天就四处漏水,然后吊一下顶,听他说的意思,好像是现在的铝扣板的那种,他还说要买一套四联组合柜……,说到这里在场的人都笑了,问他是不是要准备娶媳妇了,还有人说你就“炮吧”,可是他却不被别人的影响,仍然不紧不慢的说让我爸给算一下需要多少钱,我爸问他有多少钱,他说存折里有几千块钱,还有就是在村里和邻村给别人干活的一点零散工资,大概有两千块左右。我爸没有回答他钱够不够,而是接着问:
“二蛋”是不是准备娶媳妇了。
“二蛋”没有回答,只是深深地吸了一口烟,这时我发现一大截烟灰掉到了他的裤子上,随及他用手快速地拍了拍,他不仅没有回答我爸的问题,而是又说了一遍:
“你给我算算需要多少钱”,二蛋重复地又说了一遍。
其实,我知道他的那点钱根本就是杯水车薪,或许我爸也不想打击他发自内心的向往美好生活的美好愿望吧,所以也就把话题给岔开了,问了一些关于他娘的病情和今年的收成的话。
他和我爸是同龄人,上小学的时候就是同班同学,因为我从小就见过很多次,每次他见了我爸他们都会聊会家常,也或许就是这个原因,他才问我爸房子预算的事吧,或许,他也像莫言在“肆拾壹炮”中的主人公一样吧,他真的是一个长不大的人,或许,他的记忆仍然停留在儿时无忧无虑的快乐时光中。
这时我的眼前仿佛出现了他们儿时一起上学、一起掏鸟窝、一起玩耍的情景,他们是那样的无忧无虑,笑声、打闹声,他们是多么的快乐、自在,还是同样的山村,同样的人,然而岁月的无情使一切已经不复存在了,或许他也曾经有过这样的回忆,或许他也同样知道,童年的美好时光再也回不去了,一切美好都已然过去,现在想来真是可望而不可及了。也许他从来就未曾想过这些,只是埋着头一天一天地过生活,艰难或者是痛苦,他都无怨无悔的过着每一天。正如人们所说“烦恼都是自己给自己的压力所造成的”,也许我们说认为的烦恼,在他的世界里根本不存在,或许,他只是想着干活、挣钱,送走年迈的老娘,我甚至怀疑他根本没有想过自己的将来、自己年迈的时候应该怎么过活,在这里我似乎看到了他的晚景凄凉。
在他抽完第一根烟之后,我又递给他一根烟,他是用第一根烟的烟屁股对着第二根烟的,深吸了一口后烟就着了,或许是天越来越黑了吧,火红的烟头在我得眼前晃荡着,我甚至已经看不清他的脸了,只是一个模糊的轮廓,这时候我只能够看见烟头在眼前忽明忽暗,看不见间烟雾在是怎样在空气中慢慢消失的,我想应该和刚才一样,首先从他的嘴里、鼻孔里出来后,经过他的前额,然后进入他的发间,在头发之间盘旋缠绕游走半天后再从头发之间出来,然后缓缓的上升,慢慢的消失、消失在黑夜里、消失在山村清晰的空气里,也可能随着气流升到了山顶上,最后随着天上的云彩随风飘到了遥远的大山的外面的世界的上空,当然也有可能飘扬过海后,转了一圈又回到这个四面环山的小山村,甚至回到“二蛋”的头顶上,就像他刚从嘴里吐出来的一样。他抽了几口后,又开始了他的长篇大论,他说买一个四联门的组合柜,然后买一个席梦思的床,电视是必须买的,准备买一个三十二寸的大彩电,至于电视柜就找村里的木匠给做一个,因为他家里还有几块多年前的松木板呢。这时我爸开始说话了,
“你就炮吧” 我爸说道。
但是他说他是认真的,真的准备翻新一下老房子,等送走他的老娘之后搬回老房子住。
或许,在别人看来他说的可能不切实际,但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哪怕在别人看来一点也不靠谱,但我认为这最起码是他自己内心的一个美好愿望吧!或许,他这是在为自己的将来做最好的打算呢。
天真的黑了,他起身说要回去了,在他走后邻居们都说“二蛋,真能炮”,后来我爸给我讲了一个关于“二蛋”的炮事。那时候他们都还年轻,村里的“米柱”买了第一台私人拖拉机后,他就一直说自己也要买一台,关于买拖拉机的事他一直说了多少年了,直到现在还是时不时的提起,不过现在已经没有人再买拖拉机了,而这件事却一直成了村里人闲暇之余的笑谈了。其实,我一直认为人有梦想是对的,不管贫穷还是富有,只要我们有了属于我们自己的梦想,幸福终究会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亲临到我们的身边的,当然也包括“二蛋”。
故事到这里应该结束了吧,关于“二蛋”的事,我所知道的真的不是很多,每次回家的时候总能够遇见他至少一次,现在随着回去次数的减少,见他的机会也就少多了。有时候我一直在心里回想,回想我所知道的关于他的哪怕是短短续续的记忆,但是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了,其实也不是我想不起来了,而是回家的次数逐渐少了,以至于对于家乡的记忆似乎在某个时刻断篇了……
……………………………………………………………………………
正如莫言在《四十一炮》中所说的那样:一个“炮孩子”的想法是别人所无法去真正理解的,在他们自己的想象空间里是另外一个世界,是一个普通的、平庸的人所无法琢磨的,纵然他们的身体已经长的很大,但他的精神还没有长大。或者说他的身体已经成年、甚至老去,但他的精神还停留在少年。有人说这样的人很像一个白痴,但“二蛋”不是白痴,否则,我写的一切就真的失了存在的价值。
……………………………………………………………………………
烨雯(ywfen)
2013年3月30日 于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