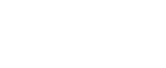父亲是一种岁月
父亲是一种岁月
我的父亲的生日是农历的二月初二。是中国农村传统节日中很重要的一个节日。 我初学写作时,曾以父亲童年为背景写过一首叙事诗。述说的是一个穷苦孩子当红军的经历。那诗开头两句是这样写的:
他出身于二月二
二月二呀!龙抬头
穷人抬头在何时
……
父亲家所在的地方叫华山,和那个著名的西岳华山同名,不是什么名山大川,是大巴山里的华山。原先是属于巴中县,后来划归了平昌县。巴中和平昌都位于大巴山的腹地,山大都以险峻而闻名。清人谢承光在那里就留下“峥嵘峭壁接青天”的诗句。水也以滩险浪激而著称。什么“风滩”、“险滩”、“生浪滩”、“望儿滩”、“鬼滩”、“神滩”……光听这些名称就足以令人生畏了。一方水土育一方人,险恶的自然环境造就出的人性格也具有坚韧、勇敢,富于造反的精神。有在中国农民起义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白莲教”起义, 有一曲“带镣长街行......”唱绝中华大地的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刘伯坚烈士。
父亲的老家华山距如今的平昌县城有四十多里山路,至今不通汽车,只能乘人工小木船行十几里的水路,余下的就尽是爬山了。那山可真高啊!就在你感觉着似乎快要到了云彩顶端的时候,突然间眼前一亮,一块好开阔的平坝子出现在面前。一笼笼翠绿的竹林端飞着群群白鹭,一片片平整的田地,静静的水面倒影着蓝天,黑黑的茅草屋顶升着袅袅的炊烟,真是有种白云深处有人家的感觉。素有“山有多高水有多高” 的大巴山区即使是在这样高高的山顶也是照样的溪水潺潺,照样的稻谷飘香。
据老家祠堂前的石碑记载: 我的祖爷最早先是从湖北的孝感迁移过来的,也就是历史上著名的人口迁移大举动,即“湖广填四川”。老家留在年迈的父亲记忆里,总是那几间破旧的茅草屋。由于年代过久,那屋子顶上已长出一簇簇荒草,厚厚的土墙上绿苔斑斑,门前是一处堰塘,到了夏天就会开出白白的、粉粉的荷花来。
父亲在家里排行老幺,也就是最后的一个。父亲的到来并没有给家里带来什么快乐和欢愉,只是给锅里那本来少得可怜的食物增添了一张嘴。父亲上面有四个哥哥,两个姐姐。不管怎样说家里太穷了!每顿饭都是让能上坡下田干活的爷爷、大爹、二爹他们先吃,到最后才轮得上屋里的女人和年幼的父亲。能吃上一顿饱饭,成了父亲童年最大的奢望。
父亲对我说:那肯定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在坡上打猪草回来的父亲,突然从一家大户人家的粮仓后墙外看见一堆白花花的大米。父亲赶紧扔下背上的背蔸,跑步过去,才发现原来是个老鼠洞。父亲用竹子做了一个长勺子,从里面往外一掏,就掏出一勺子大米。尽管那土墙很厚,足有两尺多。可这也没有难住父亲,他顽强地往外面掏着,整整地掏了一个下午,终于掏出好大一堆的大米。但是这些大米绝对不敢拿回家,爷爷的骨气父亲知道,不用说讨好,只有讨打的。可是父亲还是没有经受起一顿白米饭的诱惑,他悄悄地约出了四爹,两人到一处山坳的僻静处,用一个瓦罐,盛来清清的山泉水,烧起火,做出满满一瓦罐白米干饭……
父亲说:那是他一生中吃到的最好最香的饭。
“文革”后期,我到太行山里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小南方长大的我根本无法习惯北方的饮食习惯,作为“知识青年”,第一年享受“特供”,每月有45斤的粮食供应,其中有10%的细粮,也就是说每月有4.5斤白面,除外就是小米、玉米、高粱之类的杂粮了。 就这4.5斤白面已经足以让村上的人们羡慕不已了,他们一年辛劳下来,最多也只能分上十几斤麦子,不管怎样大米是绝对见不上的,能吃上一顿大米同样也成了我最大的奢望。
这时,父亲来了!父亲给我带来了一小口袋大米。
记得,那是一个黄昏,天上有好多瑰丽的红霞。父亲用我的小锅给我煮了一锅大米饭。他还从老乡那里买了只鸡给我炖上。鸡炖好了,清香的鸡汤上飘浮着朵朵黄色的油花。父亲给我盛了满满的一碗米饭。上面又浇上鸡汤……我让父亲也吃,他不肯。他说:他要看着我吃。在父亲慈祥的目光下,我狼吞虎咽一连吃了三大碗,直到把一小锅米饭吃得一干二净。当我发现父亲除喝了几口汤外,什么也没有吃时,真不知道该说什么才好。父亲却笑着对我说:看你这样的吃劲,我就想起我小的时候。
在散淡的月光下,踏着一条厚厚黄尘的小路,父亲给我讲述着他童年的故事……
父亲和四爹做的米饭实在是太多了! 两个未成年的孩子根本就吃不完。天黑了,到该要回家的时候,望着那余下的半罐子米饭,父亲他们实在是迈不开腿。父亲想起人们常说的一件事。在后山坳里埋葬着许多死人,而且大都是饿死的。这些饿死的人转成了饿死鬼。人只要到后山岗上去喊: 饿死人哪!饿死人哪!立刻就会感到饥肠辘辘。于是父亲和四爹两人一起到了后山岗上,大声地喊了起来:
“饿死人了!饿死人了!”
肚子撑得饱圆的俩孩子,在夜幕笼罩的荒原上,声音一高一低地喊着:“饿死人了”,那情景肯定是让人感到滑稽极了,荒唐极了。可坝子上的人们才不觉得有什么荒唐,真的以为是有饿死鬼出来游荡。次日,一大清早,坝子上一位颇有名望的绅士便杀了一口大肥猪,披红挂绿送到了后山。在那随后的人群中,跟着一个赤裸着双脚,身上的衣服襟襟绺绺的孩子,他怀着几分得意目睹自己创造出的这一杰作。那孩子就是我的父亲。
不管有多么的贫困,多么的艰难。童年总是有那么多快乐的记忆,总是让父亲难以忘怀。
我第一次回老家,是父亲带我一人回的。那年我刚刚五岁。依然是先要坐船,再爬山。那山真是太高太高。我实在是爬不动了,父亲就把我背上。在父亲宽厚的脊背上,听着父亲唱的歌子……
白鹤,白鹤,弯角角
要想妈妈就过河
……
哦!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多么令人惬意,多么令人陶醉,真的像一首流行歌曲里唱的那样:“今生今世难忘怀”。
假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生死轮回,一个人的生命真的有来生,亲爱的父亲,我愿再为您子,再为您所爱。
父亲会唱歌,尽管大都唱的是红军时代或八路军时期的老歌曲,比如《雄伟的井岗山》、《我们在太行山上》……当然,他也会唱一些旋律很优美的川北民歌。父亲的嗓子虽然有些沙哑,但是极富有音韵。深沉而不乏豪放,凝重而不失幽默,颇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意识。假若在今天,年轻的父亲也许会成为一个让人崇拜的流行歌星,也有那样一群如痴如迷的追星族。
白鹤,白鹤,弯角角
要想妈妈就过河
……
父亲记忆中的奶奶个子很高。肯定要比一般的川东北农村妇女的个子高出许多,身体也很壮实。和许许多多的劳动妇女一样,就吃苦耐劳的精神是十分令人惊诧的。她们除了要负起女人们必须做的繁重家务,养儿育女,伺候男人的劳动外,还要上坡下田的和男人做一样的田间劳动。
在父亲的记忆里,奶奶好像是从来没有睡过觉。每天早晨只要父亲刚刚一睁开眼睛,奶奶已经坐在灶前。红红的火光映照着奶奶那双永远也是布满血丝的眼睛。
有一次,奶奶在禾草堆上靠着靠着就闭上了眼睛,年幼父亲悄悄地走了过去,他非常非常想去摸一下奶奶那双青筋暴隆的手。在这种渴望强烈地折磨下的父亲终于鼓足了勇气走过去,用自己胆怯的小手在奶奶手上轻轻地抚摸了下子。奶奶的反映像是被蜂子蛰了一下。惊醒了的奶奶看看好像是做错了什么事的幺儿子,把他搂进了自己的怀里,伸出手指替父亲梳理了一下乱蓬蓬的头发。然后轻轻地叹口气,就把父亲从自己的怀里推开了。
好多年以后,直到父亲的暮年,每当父亲讲起他童年的这段往事,他的眼睛依然会变得潮湿起来。这也许是父亲生命记忆中唯一一次感受到的母爱。但就这唯一的感受也足使父亲受用了,同样也使我们受益非浅。她使得父亲对我们兄妹除了极少的严厉以外,更多的是温情和慈爱。
20世纪60年代初。正是三年困难时期,我们兄妹7人都还小,可都是年龄到了“半大小子,吃死老子”的时候。
父亲为了不让我们挨饿受饥,每天除了白天上班以外,到下班的时候就会到很远很远郊外荒山上垦荒种地,夜里总是到了半夜才回家。第二天大清早,又要赶去上班。 由于父亲的辛勤劳作,由于那些用父亲汗水换来的青菜萝卜,才使我们兄妹七人在那个饥饿的年代里,照样能够填饱肚子。
父亲从军队到地方工作,一直在交通部门做领导工作。上世纪60年代父亲在大巴山里一个叫平昌县里工作,他主持了修建平昌渭子溪大桥。记得那是一个清晨,我在睡梦里被父亲唤醒,他叫着我的名字,要带我去参加渭子溪大桥落成典礼。至今,我清晰的记得那是一个有着春天的早上,从通河和巴河上不断的飘出寒冷的晨雾,那雾非常浓,白脂一样凝固着。我们坐的是一辆苏联的嘎斯汽车,驾驶室里寒气逼人,父亲把我紧紧地搂在他的怀里,在父亲温暖的怀抱里,我好像又睡了一会,到了渭子溪新建的大桥上了,好像也有锣鼓,接下来是鞭炮,那鞭炮非常响亮,在寂静的山谷里久久地回荡着,后来是照合影的照片,100多建设者簇拥着我和父亲留下了那张极其珍贵的影像。
上世纪的70年代初,是“文革”极为动荡时期,几乎只有的政府权力机构都处于瘫痪状态,为了维系各地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转,在军队的参与下,成立了一个叫生产建设指挥部的临时机构,承担起一个地区除了政治以外的全部经济、生产、基本建设的全部任务。因为父亲有老红军的特殊身份,被当时的军管会提前“解放”出来,担任起当时达县地区生产建设指挥部负责人。他出任的第一个使命就是建设位于达县城中心位置州河上的红旗大桥,原来州河上是有一座桥的,叫铁桥。建于解放前,据说是外国人建的。由于年代已久,肯定无法满足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尽管是在动荡时期,尽管要革命,尽管每天人们喊着那些极端的口号,建桥还是必须的,就和文化大革命中间照样建设起了著名的南京长江大桥一样。达县城里开始建设第二座现代桥梁。父亲出任了是达县红旗大桥建设指挥部总指挥。在今天看来投资不到百万的工程简直就不是什么工程,可当时的100万和今天是根本无法相比的,更何况那是解放以来达县城里州河上第一座现代化桥梁,那是一座完全用石头建起来的拱形桥梁,当时没有那么多的机械设备,几乎完全依靠人工。修建红旗大桥正是达县地区的“文革”年代,喜欢做实事的父亲正好躲开了那些莫名的纷争,全部身心投入到建设大桥的工作中。父亲没有白天,没有夜晚的在工地上,我和母亲经常是到了半夜三更还必须要去给父亲送夜饭。那是一个星光灿烂的夜晚,我向父亲提出了想到工地上起看看,父亲为了满足我的好奇心,把我带上了一个正在建设的桥墩上,那是我生命里第一次站那么高去看一个的灯火阑珊的城市,看在黑夜里湍急的河流,我饱饱地呼吸着夜里清新的空气,感受着河上呼啸的寒风,工地上闪烁的灯光映照着我兴奋激动的脸庞,因为有父亲在我的身边,我没有一丝一毫的寒冷和恐惧,相反,我有几分自豪和骄傲。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达县地区早已经改名成为了达州市,就那州河上也已经建设起了好几座新的大桥。不过由父亲在那个动荡年代建设起来被称为红旗大桥依旧是达州市区里主要交通要道,不过人们在它的前面加了一个老字,叫老红旗大桥。每次我去达州城,总是会在那大桥上漫步,因为在我的心目里,这大桥就是父亲的纪念碑。
父亲的档案里,非常明确的记载着他曾经因战立下三等功8次,二等功5次,这样的记录大都是在抗战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军队有了比较系统的统计以后的数据,早期在红军时期是没有记录的。父亲是因战的二等残疾军人,他主要负伤的部位都是在腿上,小时候我和父亲在一起看着父亲腿上那斑斑弹片的痕迹,心里总觉得莫名的害怕。父亲最大的内伤是在抗战的时候肚子是,他的肠子曾经被打断过,小时候,老有人告诉我说,你爸爸肚子里接的是狗肠子,为此我还深深的痛苦过,我以后才明白,人的肠子断了根本就不要什么狗肠子替代,直接接上就可以,因为肠子在人体中是有再生功能的。
父亲军人素养非常高,无论是坐姿、站姿、走姿,他都是极其标准的军人动作。就是到了暮年的父亲腰板也是笔直提拔的。他整洁讲究,喜欢卫生,他的头发从来都是一丝不苟。无论衣服如何破旧,无论家里条件如何简陋,但是肯定是干干净净,他喜欢自己洗衣服,刷鞋子,他的黑色布鞋总是有着漂亮的白边。这是我最服气的。
父亲的勤劳是一种天性,我们兄妹一致公认:“ 父亲是我们一生中见到过的最勤快的男人。”
李保平,1958年5月,武汉大学毕业。其父李炳甲,四川平昌人,1932参加红军,曾任八路军武乡独立团副团长。其母李文英,武乡东庄人,八路军洪崖洞兵工厂女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