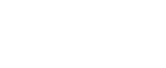汤亚汀-民族志新写作与历史重构的故事_民族音乐学与现代音乐史_译后-摘要
汤亚汀:“民族志新写作与历史重构的故事——《民族音乐学与现代音乐史》译后” 《音乐艺术》2008年3期69-73页。
收稿日期:2008-06-09
作者简介:汤亚汀(1951-),男,上海音乐学院教授(上海200031)。
中图分类号:J607;J6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4270(2008)03-0069-05
从1980年代后半期开始,西方民族音乐学界弥漫着一股反思的气氛。首先是1987年,美国民族音乐学学者赖斯质疑梅里亚姆的“观念-行为-声音”的三分模式,认为梅氏只强调社会过程,结果使民族音乐学疏远了历史音乐学所关注的问题。赖斯从象征-阐释学派的人类学家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对文化的阐释》(1973年)中的一句话得到了启示,即“象征体系……按历史构成,由社会维持,并为个人运用”。这正是他一直在寻求的音乐的“生成过程”,是社会、历史和个人这三种过程的完美结合。它回答了:人类怎样按历史构成音乐、由社会维持音乐并通过个人创造、体验音乐(Rice 1987)。他呼吁历史维度的回归,由此提出了重建民族音乐学的模式。
接着是1989年,美国民族音乐学学会麻省剑桥年会,就民族志的专题“音乐实践的表征 与表征的实践”(Ethnomusicology1990),讨论了一系列概念,其中最重要的是具有强烈文化批评色彩的“反映框架”说,即文化现象(包括音乐)本身只是非文化现象(如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学者们还自我批判了西方的制度、思想体系以及“西方中心论”。正如后来一位民族音乐学学者的评述所言:“民族音乐学,如同其姐妹学科人类学,正经历着一场对我们使命的信心危机,即对我们的‘客观性’丧失了信心。最痛苦的是,我们已逐渐将自己看作敌人、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剥削者的一分子。”这是一场旨在“建立新方法”、“推翻德高望重者”的“震动”(Becker1991)。
这一场“震动”肇始于1984年美国人类学界在新墨西哥州墨菲的研讨会“民族志文本的写作”的反思,并体现在会后出版的文集《写文化:民族志的诗学与政治》(J. Clifford, G. Marcus,1986), 以及随后的两种文化人类学专著,即:《作为文化批评的人类学》(G. Marcus, M. J. Fisher, 1986)和《文化的困境》(J. Clifford, 1988)。再早则可回溯到1970年代的一本书《文化的阐释》(C. Geertz, 1973)和一篇文章《重新评价民族音乐学学者在研究中的作用》(Gourley,1978)。因此可以说,当前民族音乐学研究的一些灵感主要来自其姐妹学科人类学的最新成果。
1990年代初始,波尔曼(Philip Bohlman, 1988)就提出了民族音乐学“思想史”
( intellectualhistory) 的概念, 一批从思想的高度总结民族音乐学历史与理论以及显示写作新范式的著述纷纷问世。其中突出的如《比较音乐学与音乐人类学》(P.Bohlman, B.Nett,l 1991),《民族音乐学导论》(H.Myers, 1991), 以及人民音乐出版社委托我们翻译的这本论文集《民族音乐学与现代音乐史》(S.Blum, P.V. Bohlman, D.M. Neuman主编, 1993,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322页)。
70 民族志新写作与历史重构的故事《音乐艺术》2008年第3期
本书由15篇小型民族志个案组成,围绕书名的关键词主题,再分为四大部分,即: (1)音乐与历史经历; (2)权威与诠释; (3)中间人与协调者; (4)音乐的再现与更新。第一部分的4篇文章,反映了音乐或其表演如何构建历史的经历——巴西苏亚人迁徙的历史;南非巴索托民工的历史;西非尼日利亚现代化和城市化的历史;比较音乐学的历史所构建的阿拉伯世界的现代化历史进程。第二部分的所谓的权威分别是:孟加拉的“嘎拉纳”音乐家弟子群,印度伊斯兰教苏菲派的世袭音乐家“格瓦尔”,秘鲁西班牙-印第安混血的梅斯蒂佐人音乐家,波兰和乌克兰的民族国家的文化机构,对前两例的历史诠释置于一种大传统与小传统互动的框架内,即北印度传统与
孟加拉传统,印度教传统
与伊斯兰教传统;对后两例的历史诠释则符合
了当今政治的需要,即现代性的民族国家的认
同。而且诠释都是“多声部”的,即当地各族群
和作者本人的多方位诠释。第三部分所谓的中
间人角色分为两类:作为东西方中介的印度音
乐家香卡(调和印度与西方传统)和法国青年
丰通(最早向西方介绍土耳其音乐),作为当地
跨部落中介的土著表演者兰利和土著音乐学家
梅德福(调和路易斯安那印第安人各社区的音
乐传统)和印度中部土著蒙达人(调和当地各
部落各种性的音乐传统)。第四部分音乐的再
现和更新,则以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的音乐和
以色列德国犹太移民的音乐为例,而略为不同
的是北美印第安黑足人两个部落歌曲的趋同现
象(可能是大众媒介传播的结果)。
至少就本书15篇文章可以看出,民族音乐学关注的“重点,已经从对音乐结构的分类、描述、解释,转向了力图理解作为文化的音乐”(Cooley 1997:11)。笔者认为,可以更加确切地说,民族音乐学关注的重点似乎大多已经从音乐学的音乐分析转向了人类学的文化阐释和文化批评,即立意已经不在音乐本体,而在音乐背后更加深层的文化与社会。所谓“大多”,即15篇文章里仅有一篇以音乐学方法分析两首印第安录音歌曲(第14篇),另外有四篇(第6、8、11、12篇)在人类学总体框架里涉及到一些音乐本体的问题。再除去第4篇是对历史事件——开罗音乐大会的记述外,其余9篇可以说完全和我们心目中的民族音乐学不一样,这些文章应该归于人类学范式,只不过是在讲有关音乐的故事,即以音乐为论题罢了。下文就本书的写作范式和历史范式做一些评述。
民族志反思与新写作
人类学经历了民族志写作的困惑,即认识论的困惑和叙事角度的困惑。前者如“对我们的‘客观性’丧失了信心”便是典型的表述。人类学家克利福德认为,民族志所描述的都是“部分的真实”(partial truth),因为人类学家个人田野工作所收集的资料总存在片面性,即总是有选择地描述,加之写作上修辞的主观性,故而不存在完全的客观事实或知识,民族志文本从来都是人们主观建构的,按照阐释学的说法,都是“真实的虚构”(true fiction),“有意识的创作”,“意义的创造”,用言词构筑所谓的“想象的社群”( mi agined community),故民族志写作又常常称为“表征”(representation)、乃至“诗学”(poetics)和“创造”( invention, creation,如时髦的说法“创造传统”[ inventing tradition]),所以民族志写作成了编造“故事”,如本书跋的标题所示。关于所谓的“故事”,克利福德的论文“论民族志比喻”认为,“比喻”(或“寓言”,allegory)即人物和事件都具有其他含义的故事。民族志是由故事构成,这些故事描述了真实的文化事件,并在道德、思想、宇宙论等方面做出相关的评述,因而其内容和形式都具有比喻的意味,故事既蕴含了不同的文化规范(即文化相对主义),又反映了共同的人类经验(即文化普同主义) (转引自庄2008:552)。“我们作为历史的故事密切联系着、而且本身也折射了我们所研究的社会的文化史”(见本书“跋”)。正如本书图里诺一文(第7篇)的结论所言:
过去发生的事情的“真实面目”是容易改变的,成为一个争议点,如何解释取决于言论者的立场和需要。历史——就像身份认同与音乐资源所附属的意义一样——在不断地被征用和重构、以满足当今政治的需要,在这层含义内,历史总是现代的。
克利福德的“论民族志比喻”和图里诺的上述引文,令人想起本文开始处所提及的格尔茨-赖斯阐释学的三分模式(1987)中的“历史构筑音乐”,其中之一即是:“对某地某时的音乐作共时性研究,即在现时研究中重建作为过去遗产的历史形式。这不是通常的借古喻今,而是反过来以今观古。“借古喻今”和“以今观古”分别与克利福德的“民族志的比喻”和图里诺的“历史总是现代的”不谋而合。
历史写作总是主观构建的。如本书作者之一西格在其文中开宗明义地如下所言:历史是以当今的视角对过去作主观的诠释,而历史事件也不是单纯地发生而已,它们还会被解读、被创造,我认为,一些社群的成员某种程度上通过音乐表演,创造了他们自己的历史、他们的现在以及他们心目击者中的未来。
知我所知,云我所云,“主观真实”(subjective truth)不可避免,实证主义不可全信。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表述并让人信服我之所知,我之所云,人类学又碰到了叙事角度的困惑,即民族志应该发出谁的声音,学者还是主宰的权威吗?那原本是一种依附于政治权威的真理权威,造成了研究者相对于被研究者一种居高临下的压迫性的权力关系。笔者认为,人类学学者就其对一种文化传统的主观阐释而言,顶多只是半个权威,一家之言而已,主要的权威,如前文所述,应是当地的音乐家或制度——印度
古典音乐家,苏菲教派音乐家,梅斯蒂佐人音乐
家,印第安土著表演者,波兰和乌克兰的民族国
家的文化机构等,他们的声音———“地方性的
话语”才是民族音乐学力图要反映和阐释的。
这样,民族志写作便从单“声部”的描述叙事风
格而成为对话式或“多声部”(polyphony)的“对
位”风格。本书中突出者如印第安土著表演者
兰利和土著音乐学家梅德福(第11篇),以及
特立尼达的印度移民(第13篇),他们犹如故
事里的人物,直接在故事进行中与作者对话,亦
即他们的声音进入并构成了民族志的写作。对
话式或“多声部”的风格拓展、打破了主位-客
位这样的二元论,进入了多元论的视角,重构了
主体-客体的关系。那是“从观察和经验主义
方法论向交流和对话认识论的重要转变”
(Scholte1987:35;转引自庄2008:555)。
“实践理论”与历史重构
1980年代以来,西方人类学产生了历史回
归的潮流。出现了两个关键词“历史”与“实
践”。先来看看“历史”,围绕它的相关概念有:
时间,过程,再生产(或再现reproduction),变
化,发展,等等。人类学理论不仅从结构和系统
向个体和实践转移,更是从静止和共时的分析
向流动和历时的分析转移。历史分析至少包括
两个趋势,其一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派,试
图联系地方性小型社会的变化和其外在的大型
地区,乃至世界历史的发展(尤其是资本主义
和殖民主义的扩张),这样首先就得承认非西
方社会的历史性。另一个趋势是民族志性质的
历史考察,关注特定社会在不同时期的内部发 展动力,当然也充分考虑外来冲击(庄2008:
643)。在本书中,第一种倾向大致反映在第2、 3、7、8、15诸篇文章里,尤其是在第三世界民族 国家的形成及其城市化的进程中,西方生活方 式和意识形态的强大影响,民族认同日益政治 化的阐释,凸现了文化批评-现代性理论中那 种政治经济学旨趣的研究倾向。民族音乐学- 音乐人类学的这种左倾政治取向,如同其姐妹 学科人类学那样,是为了让自己学科批判的声 音进入西方主流学术界、并引起人们注意。而
第1、5、6、9、11、12、13、14篇文章则大致反映了第二种趋势,所谓“大致”,即总体倾向,有时两 种趋势在同一文章里都有,如第1篇就是。 正如本文开头所述,这股历史回归的潮流
也影响了民族音乐学。这一学科自1950年代 建立伊始,便放弃了其前身比较音乐学的历时 维度,奉行“共时性的文化主义”。以往的人类 学民族志往往把被研究的文化视为没有历史和 时间观念的文化,并且用“传统”取代“历史”, 正如本文集第二篇文章“民族音乐学及传统的 意义”所揭示的:
传统的地位在土著和学术话语中是固定不变
的,是一种基本上不受历史影响的历史文化结构。 这种矛盾在哈罗德·肖伊伯的研究中体现得淋漓尽72 2008年第3期
致:他指出了非洲民俗研究基本上与历史无关的特 性。他提出:传统能“在时间维度中保持永恒”,它是 “文化积淀”的产物,而这些文化积淀在塑造自己的 时候,既排斥历史又依靠历史(Scheub 1984:4-19)。 当然,肖伊伯的错误在于混淆了历史连续性和“无时 间性”(tmi elessness)……
但1990年代以来,民族音乐学界的历史意
识空前高涨,“变化”,“反思”,“实践”,“音乐
史”成了关键词。本书的“现代音乐史”系指非 西方社会一些文化的近现代音乐史,采用了 “时空转换”、流动变迁的视角。本书作者及编 者之一布鲁姆在本书序中指出,“音乐变化是 常规,而非例外”。另一位作者兼编者博尔曼 也断言,正是故事的异质性才是民族音乐学的 标志。民族音乐学的范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 移,从对静态的封闭的地方文化研究,转变成为 对动态的开放的跨文化的研究。
美国民族音乐学家斯洛宾称之为“音乐文 民族志新写作与历史重构的故事
化的流动(flow)”,并有一系列论述,“音乐是 在地域中流动的文化,可从某一地方流动到更 大的区域乃至跨区域而传遍全球”;“世界音乐 是一系列流动的、连锁的风格、曲目与实践,地 域上能伸能缩,而不再是一系列历史、地理渊源 单一的有界实体”;“这一学科已从较陈旧的意 识形态中解放出来,在技术与传媒的运动中漂 泊不定,并为音乐创造者不断地打破地域界限 而困惑。音乐被编入文化织体之中,由日益发 展的技术所创造,由媒介传播,通过价格在市场 销售,表现出人们自律的意识形态以及对人口 迁移的控制。”(Slobin,1992)本书所有的个案 都是从互动( interaction)、流动、变化的角度来 重构历史的。
据笔者统计,15篇论述互动-变迁历史的
民族志个案中,跨城乡的有4篇(第2、3、7、8 篇),跨部落的4篇(第1、11、12、14篇),跨民族 宗教的2篇(第5、6篇),跨国度的2篇(第13、 15篇),跨东西方的3篇(第4、9、10篇)。而且 15个文本都是在跨地区的政治、经济、社会、文 化的大背景下,考量一种地方音乐文化的历史 流动景观与生态状况。如本书“序”所言,以 “音乐诠释历史”,或以“历史诠释音乐”,因为 “音乐表演(即实践)和音乐话语(即诠释)可以 再现不同的历史”,甚至“一个群体主要是其音 乐活动的产物”,“表演他者的歌曲可以展示自 己的历史格局”。这样,在人类学“实践理论” 意义上,音乐表演成为一种构建社会结构的 实践。
历史的变化来自人们的社会实践,而变化 的机制联系着社会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再生 产”(reproduction,即“再现”)的机制。让我们 再来看看80年代以来风行西方人类学界的“实 践理论”,那是由法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倾向的 哲学家、社会人类学家布迪厄所创。实践理论 探讨的是实践与社会结构(或系统,即规范、价 值、制度等体系)如何互动,尤其是实践如何再 生产(即再现)或改变社会结构,因而社会文化
实践———在民族音乐学领域则是表演实践——— 成为变化的中介。而且“音乐实践通过时间展 开,直接体现时间过程”:“通过音乐塑造的时 间过程,强有力地、富有意义地密切联系着特定 社会和文化空间的变化经历,鲜明地表现在殖 民化、民族国家的形成以及相关的移民运动
中”(Stokes 2000:394)。因此,民族音乐学也将
“实践理论”当作音乐史研究的指导性的思想
定式。如本书“跋”所言:
沃特曼则考虑“延续和变化”之间的关系(这种
关系本身有点经典地表达了也可称为现代主义的那
种基调),他显然是理论性的文章鼓励我们将“实践
理论”当作音乐史研究的指导性的思想定式(formu-
lation)。文化的延续性,不是静态的,而是反复发生
的。实践“反馈于结构”,当“行为者面临矛盾”的时
候,结构发生变形。透过这层黑格尔式的“迷雾”,沃
特曼发现“对特定风格的历史发展最令人信服的阐
述涉及到音乐实践,因为音乐实践受制于、也有助于
形成社会互动和文化秩序的必然(emergent)格局。”
其实实践-结构的互动已经暗含在梅里亚
姆1964年的“观念-行为-声音”的三分模式
里了。因为他认为,通过表演行为(即实践)展
示的声音如果符合传统观念(即结构),那么下
一次行为得以维持,这便是传统(稳定的力
量),若不符合观念,行为(实践)和声音就会改
变(变化的力量),甚至如后来内特尔所说的,
最终再造成观念的变化。
在本书,“实践理论”的两套互相关联的术音乐艺术民族志新写作与历史重构的故事73 语几乎见之于全书每一篇文章,一套是关于活
动的:实践,行为,互动,经历,表演,诠释,再生
产;另一套是活动的人:中介(或协调者),行为
者,个体,主体,客体(部分参见庄2008:633)。
再来看看本书一再提到的意识与文化的
“再生产”(本书译作“再现”)的问题,人类学
一直关注社会结构和价值体系是如何被行为者
再生产的。社会实践中最突出的便是仪式,象
征人类学认为仪式是意识再生产的首要母体之
一,通过仪式,行为者接受特定文化的规范和价
值,或至少暂时去除可能的异端思想和情感。
人类学结构马克思主义也很重视仪式的力量,
认为它能调和社会结构的冲突(参见庄2008:
640)。注意本书“序”也有相同的说法———“音
乐用来调和对立的观念和生活方式”。就仪式
而言,全书半数以上,即有8篇文章涉及到仪
式,分别来自北美印第安土著宗教、北印度的印
度教、印度-孟加拉的伊斯兰教苏菲教派、特立
尼达印度移民的印度文化仪式,基督教-犹太
文化仪式。这些仪式都调和了对立的部落、族
群、社群、宗教、文化,促成了这些实体的互动或
跨越或混合,例如北美印第安泛部落的音乐文
化,北印度泛部落-种性的音乐文化,印度教与
伊斯兰教音乐文化的交互,特立尼达印度、东印
度、西印度群岛和西方诸音乐文化的多元混合,
以色列德国犹太族群借用基督教古典音乐文化
所实行的越界。
最后要说明的是,本书翻译中最大的难点
是术语,一方面是牵扯到的民族、文化较多,如
北美和南美印第安、南非莱索托、西非约鲁巴、
阿拉伯、土耳其、北印度、孟加拉、秘鲁印第安和
西-印混血的梅斯蒂佐、波兰-乌克兰、特立尼
达印度移民、犹太德国移民,造成大量的人名、
地名、宗教、音乐术语等专名的音译的困难,许
多都没有现成译名,只能一个一个音地查找以
前新华社的多语种外汉对照表来“杜撰”。同
时译者为了读者阅读的顺畅,尽量避免出现过
多的地方性术语,比如以意译代替,将术语原文
置于后面括号内。
另一方面是人类学、文化批评、后现代的等
西方新学的许多术语在全书反复出现,无法回
避,造成移译的困难。虽然许多术语在我国社
会科学界已经有现成译名,但不少词放入具体
汉语语境中似乎难以理解,我想这也许是许多
社科新学译著难以理解的一个重要原因吧。按
照“达”即可读性的原则,我们在译文中作了一
些调整,并在括号里列出原文及已有译名,如
negotiation,“协商”转换为“协调”(即强势群体
与弱势群体之间较量及互相妥协的过程); re-
production,“再生产”转换为“再现”;
internalize,“内化”转换为“接受为自我的意
识”。另外有一些似乎可以理解,则作了保留,
如representation,“表征”(意为“表述及象
征”); acculturation,“文化涵化”; appropriation,
“文化征用”。还有一些一般社科译著常有误
译,便根据手头的人类学词典加以纠正,如rites
ofpassage,误“通过仪式”,正“生命仪式”。最
后有些根据语境作不同处理,如community,有
时是“社区”(具体存在的地域实体),有时是
“社群”(非实体,相当于“特定的一群人”
[group]),有时是“社团”(具体的团体),有人
翻译为“共同体”,似乎概念过大(如“欧盟”,
“英联邦”),在本书语境中不妥。
参考文献:
1. J. Becker,“A BriefNote on Turtles,Claptrap and Ethnomusicology”.Ethnomucology1991/3.
2. P. Bohlman, “TraditionalMusic and Cultural Identity: PersistentParadigm in the History of
Ethnomusicology”, YearBook for Traditional Music 1988.
3. T. Cooley,“Casting Shadows in the Field: An Introduction”, Shadows in the File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7.
4. T. Rice,“Towards Remodeling Ethnomusicology”, Ethnomusicology 1987/3.
“Representation of Musical Practice and Practice of Representation”, Ethnomusicology1990/3.
5. M. Slobin,“Micromusics of theWest:A Comparative Approach,” Ethnomusicology1992/1(摘译参见《中国音乐学》1994/1).
6. M. Stokes,“Ethnomusicology”, in New Grove Dictionary of Music and Musicians(2nd), Macmillan 2000
庄孔韶主编:《人类学经典导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