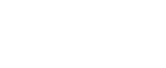陈年往事
去年,我回老家在表哥孙子的婚礼上见到了伯母,她是我父亲面上的唯一在世亲人。说是亲人我都会恶心,因为在我幼小的心灵里她可是一个恶魔泼妇。
老家的婚礼依然保持着浓重的乡土味。有厨艺的亲朋掌勺,有体力的好友端菜,靓女酷男担当起斟酒沏茶活儿。婚宴现场“乌烟瘴气”、“哄闹嘈杂”、“唾沫横飞”,但是每个人好享受这种氛围,每张脸上都洋溢着喜庆的愉悦,就连猫狗都知道今天村里有喜事,它们成群结队而来,在桌子底下安静地分享属于它们的那份宴席。那天,村子里的任何人都不用做饭,也不用费心着装,到了饭点,放下农活,找个空位置坐下吃就是了。老家的这个风俗一直延续至今。如果现场谁能说上个把荤段子,那TA绝对能盖过新郎新娘的风采,吸引无数围观,不用担心这种行为会遭到主人家的白眼,农村婚宴图得就是一个“闹”字。
在人群中有一位老妇人一直瞅着我,表哥告诉我她是你的伯母。
“伯母,她还没死?”
父亲去世的最早,不擅言语,手里没活就坐立不安的伯伯几年前也死了,可是老天却让这位女婆还留在人间。不是有“好有好报,作恶坏死”的说法吗?诸如此类的事情见多了,我有时也会对上帝起疑心。
我抬起头双眼聚焦在她的脸上---儿时从来不敢这样地正视她---艰辛的岁月全部刻在这张脸上,满脸皱褶,肌肤黝黑,一副孤寂无援的神态,不管周围怎样热闹,也点燃不起她一丝的快乐,她就似一个局外人,默默地坐在一角望着我。在这个场子里,她分明只对我有兴趣,我们四目相对,我发现她嘴唇有颤抖,是老人不已的那种颤抖,还是在喃喃自语,我不晓得,离得有好几张桌子距离。可是我怎么看都不能将眼前的这位老妪与我记忆里的她同日而语。
奶奶生有两个儿子,伯伯和我父亲。由于她的一个决定,兄弟俩从此走上了迥然不同的人生,也就此结下了伯母和我们一家的冤仇。姑奶奶在上海做生意,需要一个下手,再三考虑之后奶奶把我父亲送去了上海,姐姐出生在老家,我和妹妹诞生于上海。
从此,她就成了一个我们家谁都不想见到的女人。每次去奶奶家,我想方设法回避她,不敢与她正视,她的眼神如锋利的剑会刺伤我幼小的心脏。孩子能想到的恶作剧她都会使。在我午睡时,她会抓一把蚊子放进蚊帐里;你在认真做暑假作业,她会在你背后装出失手打碎玻璃瓶之类东西,有一次被她吓得发了一个星期的高烧。她恐吓我们的手段远远不止这些,农民一个,字也认不上十个,指桑骂槐技巧可谓登峰造极,奶奶常常哆嗦地把我揉在怀里暗暗流泪。
因为这个女人,我们对伯伯一家也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分,每年回老家时都住外婆家,只是去看奶奶时,顺便问好一下伯伯,久而久之与伯伯疏远了,堂兄结婚我们也没有接到通知,更为不可饶恕的,奶奶去世,伯伯去世她都不让我们知晓,那时父亲已经去世了。
我真不知道她还活着,我更没想到这些陈年往事还记得如此清晰在目。
一种莫名,血拼命往上涌,我要走到她跟前,指着她的脑门像她从前骂我们那样的诅咒她一番,以解半个世纪的那份恨。但是,让我纳闷的是,那天我居然恨不起她来,非但如此,心底里还腾起一丝怜悯。我想走近她,再近点看看她,可是,脚怎么也提不起,灌满了铅似的重。
受人无端指责,被人恶作剧侮辱固然是件很不幸的事情,但是我也未曾尝到记住这桩陈年往事而有一丝幸福的感觉。人不就是在犯错和纠错的过程中成长,在笑别人,又被别人笑的过程中走完一生的吗?望着这位老人,心里的天平开始向她倾斜,半个世纪的恩怨终于在那刻出现了松动,我迈出第一步,朝她走去。她也在慢慢挪动身子做好迎接我的准备。
“王弟弟,”她叫了一声我的乳名,伸手紧紧地握着我。“你都有白发了……”
我想叫她一声“伯母”,这两个字到喉咙口最后还是咽了回去,记忆里从未这样叫过她一次。她握着我的手,始终没有松开,我有察觉,接下来她将跟我说的话,我抢在她先,说,今天是高兴日子,我们不谈那些陈年往事。
这是一双劳动人的手,坚硬、毛糙,指甲里永存着洗不干净的泥土黑。这双手将是那个年代的绝笔,从今往后,我们不会再见到如此厚重的手。我原以为她的手应该是冰凉冰凉的,不料有温度,在我幼小心灵中她给我留下的那份恐惧痕迹,在这份温度下被消融了,眼前的她梦幻般地变成了一位让人极其容易生起怜悯之情的孤寂老人。
我说,坐下吧,站着不累吗?她这才放下我的手,说该回家了。我送她走出院子,她每跨出一步竟然有那么费劲,表哥说,三年前她摔了一跤,据说盆骨还是肋骨断了几根,常年卧床。听说我来了,她才硬撑着今天过来的。
狭窄的田埂上,一个黑点缓缓地在挪动,我在院子门口望着她的背影,都站酸了腰,她还在走,那行走速度让我想起了田埂上爬行的蜗牛,前方的黑点陡然变得模糊不清,原来我流泪了。
“伯母,”我一个箭步冲进了黑夜,“我送你。”
(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