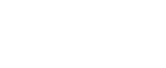砍山
砍山
作者:曼青
1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川西大渡河畔的一个小村庄。
水是那样的清,清得可以看见里面游来游去的鱼儿。
山是那样的青,青得满目苍翠,林中松鼠蹿跳、鸟儿惬意飞翔。
村民质朴而热情,晨耕暮收,处处可见炊烟袅袅的农耕生活美景。
这个唤做小水的村庄,村民分两段而居。村尾的一段被隔着山梁甩到了几里开外,村头这一段离县城大约两里路模样,是被大渡河水冲刷出来的一个小小滩涂所在,只零星座落着几户农家。
一日,村头山脚一处稍微平坦的所在,突然来了两个身影,看中此处所在后,便开始忙碌起来。不几日,村民们就发现这块无主的荒地上,竟然像模像样用木板和茅草搭起间小小的房屋。
彼时,并无严格的建房约束。村民忙碌自己的营生,荒地无主也无人上前阻止。
小茅屋里走出来一男一女,男的披着“擦耳瓦”,女的穿着百褶七彩裙。
“倮倮下山了——”最先发现这一状况的,是放牛的二狗子。二狗子年岁不大,脑子里大约还尚残存着幼时大人的恐吓:“不听话哇,不听话等倮倮用擦耳瓦把你裹起,背上山去当‘儿娃子’”。因此,惊恐之下二狗子连牛也顾不上牵,一路咋呼着就往路边冲,并将这消息迅速传遍沿路而居的几户人家。
川西山间,原本就是彝汉杂居地带,历史上曾有过彝人抢去汉人小孩,充做奴役的现象。虽然八十年代的川西早已不存在这样的情况,但由于民族间沟通交流匮乏,彼此不了解,猜忌、防备之心仍然严重,当地汉人仍旧称呼彝人为“倮倮”。
当然,时隔三十年后的今日,若再回到这座村庄,你会发现彝汉之间已经完全和谐交融。但在当时,“倮倮下山了”仍是杂居地带汉人制约不听话孩子最管用的话语。
“倮倮”下山了?怀着疑问聚集到一起的村民们正在窃语议论时,那一男一女已牵着二狗子慌乱之中丢下的牛,一路跟着找寻过来。
………
2
众人抬头这一望眼,却突然停止窃语安静下来。
“这阿米子长得巴适起在哦……..”不知道是谁轻轻先开了口。
“硬是巴适得很哦……”马上就有人赞同应和道:“简直就像电影里头的那个阿诗玛,哪哈来的这么巴适的阿米子……”
“阿诗玛”与山下汉家妹儿相比又是另一种美,肤色黑中透红,鼻梁高挺,双眸黑得透亮,嘴型分明,大小正好,整个五官搭配在一起,犹如一朵盛开的映山红,红得正艳、美得夺目。
“阿诗玛”身边的“阿黑哥”,显然不情愿眼前这些人盯着自己的“阿诗玛”没完没了。嘴角刚还挂着的友好笑意,不觉就不见了踪影。气咻咻的“阿黑哥”把缰绳准确无误塞到被二狗子紧紧拽住衣角的桂婶子手中后,拉了“阿诗玛”就转身离去。
“哎——”桂婶子紧跟上前两步,有些不好意思的想要张嘴说点什么,但怎么也追不上“阿黑哥”牵着“阿诗玛”飞快的步伐。桂婶子身后,是众人一片怅然若失的叹息:“怎么走这么快,话都没说一句就走了…….”
3
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彝族小伙子是足够勤劳勇敢的,就像漫山开遍的映山红,一树一树的葱茏青翠——“阿黑哥”其实是个很英俊挺拔的彝族小伙子,名字唤做“阿呷”。
山是青的,水是绿的,彝族阿米子是足够美丽善良的,就像漫山开遍的映山红,一树一树的芬芳艳丽——“阿诗玛”其实是个普通而美丽的彝族姑娘,名字唤作“阿伽”。
桂婶子是个热心人,自打那日还牛事件过后,总爱背起背篓就到阿呷夫妇的小茅屋前后割猪草。阿呷和阿伽的小屋里里外外空落落,一无所有的模样。年轻力壮的阿呷不等小茅屋彻底修整好,就肩背斧头每日早早出门砍山。
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大山里的汉子除了在泥土中寻活外,能贴补点家用的也只有在山里打转了。吃不得苦的,就到山里挖点虫草、捡点蘑菇。吃得苦的,就下力上山砍柴禾,俗称“砍山”。
砍山的汉子中胆大的常做了非法的活计——砍树卖木材,胆小守规矩的则老老实实砍些不成材的柴禾树,卖柴贴补家中生活。两类砍山汉子的共同点,都是在崇山峻岭中讨生活,都要承担大山中那些未可知的风险。有时候,他们付出的不仅仅是汗水,还有可能是一条胳膊或一条腿的残缺人生,更甚而至生命……
柴禾是这山下村民通用的燃料,这能帮阿呷换回钱粮,维持俩人的生活。阿呷每日早早出门便是做了这砍山的汉子,而阿伽在短短的日子里,竟慢慢就显出了身孕的模样。时常来割猪草的桂婶子经验丰富,一眼就明了是怎么回事。看着阿伽一个人手提重物,拾掇着小木屋,桂婶子不觉心生怜悯,有时就干脆放下背篓帮她做些事情。日子久了,桂婶子大概能完全弄清楚那些关于阿呷夫妇的往事。
阿呷是一个尚在封闭中的彝族部落头人的儿子,家里还保有着一些最初是娃子,后与当地彝人通婚生活下来并留下后人的汉人。这或许也是阿呷会“汉话”,连带着阿伽一并结结巴巴能和桂婶子交流的原因。
头人在阿呷五岁的时候,就按风俗习惯为他娶进二十岁的新娘。等到阿呷逐渐长成一个器宇轩昂的俊小伙,他那颗懵懂的心却毫无保留给了部落里一朵盛开在贫穷白彝家的映山红——阿伽。
阿呷和阿伽的爱恋不被祝福和认可。就在头人勒令懦弱的阿伽父母尽快将阿伽嫁出,要掐断俩人之间任何往来可能的时候,阿呷做出了大胆的决定。在一个圆圆的月夜,这个全身充满反叛家族力量的彝族小伙带着他心爱的人儿,逃下山辗转来到了这块离县城政府已不远的村庄。
对于山下汉人和政府的忌惮,足以抑制头人的追索念头,确保阿呷和阿伽俩人的幸福继续……
4
日子在平淡中前进,阿呷和阿伽的小屋渐变了模样。阿呷相当勤奋,他有一身好劳力和挥洒不尽的汗珠,赶在阿伽生产前,竟将小屋里里外外添置满了生活所需。
阿呷和阿伽的第一个孩子,在冬天的严寒来临时降临到这个世界。
村民们看到了阿呷和阿伽脸上满足的笑容,听到了孩子的啼哭欢笑。慢慢的,在桂婶子的牵线搭桥下,阿呷和阿伽夫妇俩逐渐融入到村庄里。俩人勤劳的身影,成了村民们教育孩子时常挂在嘴边的鞭策:你看人家阿呷和阿伽俩口子好勤快,你们这些懒娃儿些几哈点做事情且得了……..
随着大一点的孩子开始蹒跚学步,阿呷和阿伽夫妇的第二个孩子也紧接着降世。小一点的孩子蹒跚学步的时候,大一点的孩子已经能跟着村中的其他小孩嬉闹玩耍。村民们很快又发现了不同:大一点的孩子和阿呷、阿伽对话时用彝语,而和村中孩童说话时却是一口地道的汉话。于是不觉又夸赞起大一点的孩子聪明,会两种语言。
相对于村民各家多年来小有积蓄,阿呷和阿伽的日子始终是紧巴巴的。彝人高居山上,并不善于耕种水田,阿呷和阿伽对于庄稼的耕种,只限于在屋子周围开垦荒地,种植包谷。要养活一家四口,这点包谷显然不现实,更何况阿伽开始在小屋后养猪喂鸡,这些都需要粮食。
于是,阿呷每日砍山爬得更高、攀得更险了,为了多砍柴换钱回家,他身上如若有九牛二虎之力必然也是要全部使出来的。家中嗷嗷待哺的孩子和美丽温柔的阿伽,是他完全付出的动力。
阿伽的身影也更加忙碌,村民们常见她背上背着老二,手中牵着老大,就忙着出门割猪草,或者蹲在包谷地里扯草浇粪。
岁月的风霜扑上了他们的脸庞,阿呷更加瘦削了,但黝黑手臂上、腿上的肌肉愈加蓬勃鼓起,他把身体所有的能量都集中在了这些部位。阿伽头发没有刚来时黝亮了,微微干涩的辫子凌乱挽盘在头顶,原本黑中透红的脸蛋也失去了最初的红润。
日子虽苦,但村民们却发现夫妻俩笑的时候更多了,还能感觉到那种舒畅发自内心。对于阿呷和阿伽来说,男耕女织、相依相伴,这或许就是最幸福的生活。对于物质或其他,他们并没有太多的奢求和欲望………
5
映山红花开红艳艳,那是杜鹃啼血染就的花朵。
大山巅上那笼青岗树枝桠繁茂,那样的绿,绿得晃眼。绿得吸引着山鹰围绕着盘旋,绿得牵引着阿呷铆足了劲,将手臂和腿部的肌肉完全鼓动起来,向着它攀援而上。
没有人知道阿呷在看到如此巨大、繁茂的一笼青岗树时,脑子中是否显现出了阿伽一直希望拥有的一头小牛犊的影子。能养上牛对于山上的彝家来说,那是富足生活的象征。彝家凡重大祭祀,那是要杀牛作供品的;彝家婚嫁,能举行牛宴,那也是很有光彩的事;就连彝家身后火葬,如能有牛招待亲友,那也是能颇慰死者身后的。
没有人知道阿呷在看到如此巨大、繁茂的一笼青岗树时,脑中是否显现出两个孩子背着书包和周围汉家小孩一样上学堂时的情形。阿呷的目光透过书包看到了新的希望。
那天早晨,阿伽感到一阵莫名的不安,在薄雾遮掩的晨光中送阿呷出门时,她特意细心的将阿呷擦耳瓦系绳结绕打牢,还捡起石块将不停聒噪的老鸦撵走。出事后,阿伽十分后悔自己什么都做了,唯一没做的便是挽留住阿呷,不让他在不吉利的兆头下还去砍山。
山鹰飞得累了,它准备要歇歇脚。
它盘旋往复,终于相中遨翔天际发现的一笼最好的丛林。
阿呷爬得累了,他准备要歇歇气。
他穿梭寻觅,却突然发现一生中看到最茂盛的一笼青岗树林。看这长势,怕是很多年没有被别的砍山人寻到。
青岗树成树一般粗若成年男子臂膀,是柴禾时代最理想的燃料。青岗树木质结实,燃烧旺盛而持久,烧就的木炭也同样具有这两样优点,被人们当作煤炭之外的上乘燃料。其价格比一般的普通柴禾要高上些许,这也是青岗树深受砍山人亲睐的原因之一,久而久之,矮一点山上青岗树成树越来越少…….
这一笼依峭壁而生长的青岗树就这样随风摇曳着茂密枝叶,仿佛在呼唤着阿呷。阿呷虽也看到了那险隘地势,但这一丛青岗树若是能砍下,足以换一笔大钱,大到解决眼前家中的困境,并带来转机与希望——这个念头在阿呷脑中反复盘旋,并越来越强烈。终于,阿呷的犹豫消失了,他仿佛突然被灌注满无穷力量,向着峭壁上青岗树林攀援而上…….
二狗子老汉和村中几名砍山汉,这一天也在砍山。另一片梁上的他们,转身歇气的时候,突然远远就望见一只黑色的山鹰,张开羽翼,坠崖而落——
二狗子老汉擦擦眼睛,又回头望了望猝然呆住的同伴,发现这并不是自己的幻觉。那黑色身影除了日日砍山的阿呷还会是谁,黑色擦耳瓦在坠崖瞬间像极了山鹰突然张开的翅膀……
………
6
阿伽将永远睡着的阿呷独自留在小屋,带着两个孩子不知所终了。
二狗子老汉带着几个结伴砍山的汉子,翻下沟壑将阿呷尸身寻得送回小茅屋后,熬不住困乏,说好第二日过来帮忙,然后离去。
第二日一早,党二狗子老汉带着桂婶子和乡亲过来帮忙料理后事的时候,却突然发现阿伽和两个孩子不见了踪影。阿呷倒是一身干净打扮,静静躺在屋内。
“这倮倮女子咋这么狠心!”村民们见状纷纷议论不休:“男人还躺在那,她倒自己就跑了……是不是外头早有相好的了…….”
桂婶子和阿伽接触最多,她清楚阿伽不是薄情寡义的人,但此情景下也无法出声反驳。
“这下可咋办才好?”村民面对没了主人家的丧事,没了抓拿:“这.......怕是不敢动阿呷得……”
“要给他家里带个信吧,我们又不晓得他究竟从哪哈来的…….”其中一个村民说着突然想到什么,盯着桂婶子正要询问,却得到了桂婶子一副我也不晓得的否定神情。
“算了算了,我们不要管了,回去了…….”说话的是长贵老汉:“这种事乱帮不得,前年隔壁村富贵家就是和一个倮倮打伙做生意,结果出门遭了车祸,倮倮死了,富贵瘫了。这本怪不得富贵,但倮倮家来人把富贵家的猪、牛拉走了,家具啥的扛走了,还赖在他家吃了大半年的‘杠丧’,富贵家现在那个惨……..”
“就是就是…….”人群中一大片附和的声音,富贵家的教训太深刻了,这附近几个村的人几乎全部知道这回事。说话间,已有人挪动脚步想要离开茅屋,这世道就怕碰到扯不清的,老百姓谁愿意往自个儿身上揽事呢。
“好吧……”带人来的二狗子老汉不得不说话了:“我们先回去等哈,万一阿伽是回老家去报信了呢,如果是那样,也应就在这一两天回来,到时候就咋都好办了…….”
“哧,我看那女人就是跟野汉子跑了,还指望她回来……”人群中有人不相信的嗤笑:“这么大热的天,我看倒只有把阿呷留在屋头沤蛆了!”
二狗子老头闻言不觉摇摇头,拉着一副不忍模样的桂婶子,最后把门带上,怏怏回家……..
7
“阿伽被绑回来啦…….”
不过半天时间,这讯息就如同秋天里的一阵凉风,迅速拂过小村庄这几户零星人家。
哪个绑回来的?怎么这样快?怀揣着一个个疑问,村民们一股脑往小茅屋跑去。他们想要看看这个在自家男人尚未入土为安就跑掉的“倮倮”女人,他们好奇会不会同时绑回来那个他们揣测中的野汉子。
然而,他们却走不进小茅屋,也看不到绑回来的究竟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远远的,他们就听到了小茅屋里阿伽一声声凄厉的哭喊声、皮鞭声以及一个彝族汉子的怒吼声。阿伽的两个孩子睁大了惊恐的双眼,被几个彝人汉子辖制在小茅屋外。
二狗子老汉见状也不由发怵,带着众村民正要上前询问,却被毫不客气从小茅屋跟前撵走。
越来越多的彝人聚集到小茅屋周围的空地上,不愿惹麻烦的村民们选择远远避开这个突然冒出如此之多黑压压人头的小茅屋。
那天的夜尤其黑,黑得伸手不见五指。那天的夜十分静,静得住在百米开外的桂婶子一家能够清楚听到阿伽凄厉并渐嘶哑的哭叫声。小茅屋外鼎沸的人声渐渐消歇下来,夜太深了,深得让兴奋了一天的他们沉沉入睡。只有从山上牵来的牛,扛来的大铁锅孤零零被甩在场中,等待着黎明。
后半夜,一个用擦耳瓦蒙过头顶的宽大身影,轻轻从小茅屋外某个角落走出,悄悄一路过来敲开了桂婶子的门。没多一会儿后,二狗子老汉打开门小心翼翼将这个有点怪异的身影送出。身影没有再停留,果敢包裹着什么迅速离开了村庄。
偶尔几声老鸦叫声凄厉的划破夜空,远远飘散开来。这样的夜晚,有些糁人,桂婶子几乎一夜没能睡着——二狗子老汉做主送走了神秘擦耳瓦,桂婶子却将擦耳瓦带过来的那些话语在心里反复折腾了一夜…….
……….
8
第二天一早,桂婶子挎上了背篓,忐忑着往小茅屋走来。明显皮泡眼肿的她,边走边在心中不停念叨:“我只是去割猪草,这群天杀的总不可能把我吃了哇……..”
小茅屋外一早就沸腾开来,人头一阵骚动。居高的地势让桂婶子很快瞅清场中情形。一个彝人老头正暴怒的站在场中,嘴里吆喝着桂婶子听不懂的话语,很快,一拨七八个人分散四下搜寻而出。
桂婶子一看就明白,这是在找晚上那个敲自家门的神秘擦耳瓦呢。桂婶子心中一阵担心,嘴里不由习惯性嘟囔着:阿弥陀佛,菩萨保佑可别再让抓回来了……..
随着四散搜寻的人离开,气咻咻的彝人小老头,弓下身子就着尚有余烬的柴灰,点燃一根烧得有些黑得油腻的烟杆。很快,就有人往他身后抬过来根板凳,供他坐下歇息。
桂婶子很快发现自己的担心有些多余,没有人会注意茅屋后高处心不在焉割着猪草的她。此时,场中众人的目光全都带着畏惧盯着抽烟的彝人老头,等候他的吩咐。
小老头黑黑的面庞由于衰老皱成一团,抽着茄儿烟(茄儿烟:川西山间村民自制的本地土烟,气味浓烈。)不时吐出两泡黏糊的口水,桂婶子甚至能依稀看到他焦黄而残缺的门牙。他身上披着的擦耳瓦并没有染过,原本是羊毛本色,这会由于污垢已经不怎么分辨得出原本颜色。
一锅茄儿烟下肚后,小老头精神仿佛突然涨高了许多。抬起烟杆在脚下砰砰磕掉残渣,立起身来一阵吆喝。很快,小茅屋前的人们开始抬锅的抬锅,赶牛的赶牛,动了起来。
翻下小坎坡,过了公路就是大渡河岸,桂婶子顺着众人行进的这个方向望去,不由一阵心惊胆战,嘴里不由又喃喃念道:阿弥陀佛,可怜的阿呷,怪不得昨晚老鸦呱了一晚上…….
大渡河水还是那样滚滚向东流去,空旷的河岸边仍是那些嶙峋河石。河石大小不一,大而平整一些的能够容纳数人,小的或只能站立一人。一处稍微平整点的河石上,不知何时已经燃尽了一堆篝火,而篝火旁摆放着阿呷的尸身。
一件黑色的擦耳瓦从上往下覆盖着阿呷,由于擦耳瓦并不够长,阿呷两条腿并无遮拦孤零零的露在外面。有几名彝人围着火堆半躺在软和的河沙中,这时远远见了大队人群往河边过来,赶紧起身查看篝火,往里面添加柴禾……
……..
9
桂婶子心中念叨半晌佛,这才想起今天过来的目的,蹑手蹑脚往小茅屋靠拢——眼下人都往河边而去,桂婶子仔细一路看,并没有见到阿伽的身影,阿伽一定还在茅屋中。
桂婶子并不往门的方向靠,她很熟悉这间小茅屋的构造。桂婶子轻手轻脚的从草地上梭到茅屋檐口,把身上的背篓放下,刚趴到木板缝上,嘴巴就立即张大了再合不上。
半晌,桂婶子口中才有声音出来,不过她却不再念佛,反复牙恨恨的诅咒:这天杀的!这天杀的…….然后,迅速绕到门前,推门进了茅屋。
阿伽被捆绑了手脚丢在床上,全身上下血迹斑斑,没有一块完整的地方。床上单薄的被褥凌乱不堪,阿伽被撕烂的衣服揉成一团丢在床前。
桂婶子眼中不觉浸满泪水,她上前扶起目光呆滞的阿伽,想要把她身上的绳索解开。阿伽倒是还不糊涂,呆滞的眼珠子滚动了一下就定定盯着桂婶子,像是要开口说什么,可只见她嘴唇翻动,桂婶子却听不到一丁点的声音。
桂婶子眼前晃过昨晚上那个擦耳瓦的影子,立即明白了什么,赶紧自己先开口把阿伽最想听到的消息道出:“阿伽,你不要担心,你的两个娃儿,已经被你妹妹带起连夜走了…….你现在还能走不……...”
桂婶子看当下情形,已经是下定决心不再畏惧,无论如何也要帮助阿伽逃出。然而阿伽并不要桂婶子帮他解开绳索,反而用目光示意桂婶子赶紧离开。
“你……”桂婶子这下完全迷糊,晚上那个神秘擦耳瓦是阿伽的妹妹阿美裹着两个孩子前来求助,想把孩子借放在桂婶子家,然后再折回来救姐姐阿伽。桂婶子的男人,也就是二狗子老汉生怕惹事上身,无情拒绝了阿美。
也正是阿美,桂婶子才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
10
那日阿呷被抬回来时,正好被下山赶场的族人撞见,族人当即赶回去禀报头人。头人一得到消息,马上就带领族人浩浩荡荡赶下山来,要按彝人风俗接收阿呷遗产,包括“接收”阿伽。
彝人古老的婚嫁风俗中,儿子死了,父兄接收未亡人做老婆,这是旧时为了防止家族财产外流的一种方法,在大小凉山中均存在此种叫做“转房”的婚嫁习俗。(备注:建国后随着时代发展,转房婚嫁习俗在慢慢失去生存土壤。但个世纪八十年代的大渡河畔,这样的风俗还存在,酿成了阿伽的悲剧。)
有好心人一边急着跑来把消息告诉阿伽,一边也把消息带给阿伽的妹妹阿美。阿伽当初既然选择和阿呷一起逃到山下过自己的日子,自然不愿坐等暮暮垂老的头人来接收自己。阿伽含泪撇下阿呷,带着两个儿子仓皇奔逃。
这就是第二天二狗子老汉带着村民过来帮忙,却不见阿伽和两个孩子的原因。
可惜的是,头人半路将阿伽母子截住,立时给绑了回来。阿伽随头人如何鞭笞均,均不同意被转房。头人将阿呷搬移到河边后,用强在小茅屋内急急将生米做成了熟饭。
彝人身后一般实施火葬,当熊熊烈焰燃起时,亡者的灵魂就能随之升到天上,得到超脱和永生。就在桂婶子焦急想要再劝万念俱灰的阿伽抓住机会逃走时。河边为阿呷搭建的火堆已经成形,用做招待族人的牛也已经宰杀出来,被切割成一大块一大块的扔进了沸腾的盐水锅。
桂婶子耳边远远传来话语声,她赶紧起身往门外瞅去,只见两个彝人正朝茅走来。阿伽也听到了这声音,神色仓皇用捆绑着的手肘拐了拐愣住的桂婶子,示意她赶快离开。
桂婶子无奈之下只得赶紧从茅屋窜出,背上背篓赶紧爬到屋后高处,假装割着自己的猪草。那天桂婶子是最后看见阿伽,片刻过后,穿戴整齐的阿伽在一左一右的护持下走向河边。
桂婶子见此情形,明白自己已经帮不上任何忙,背着几根猪草的她感觉到背篓从未有过的沉重,往家走的桂婶子边走边念佛:这一直是阿伽族内的一种习俗,或许这就是阿伽注定的命……
11
阿伽最终没有转房到头人手里。
这消息是桂婶子的儿子二狗子随后带回的。
二狗子年纪尚小,非常好奇彝人举行葬礼的过程。拽着几个小伙伴,壮了胆子,就趴在河边大石包后,远远观望河边的情形。
河边哪里有可以遮挡身形的大石包,再没有比这一群成天在河边淘气的半大小子清楚。因此,二狗子和小伙伴直到离开,也没有被举行葬礼的人发现。
牛肉在沸腾的咸盐水里煮着,慢慢就散发出香味来。这几乎就要诱惑着平时不多见肉星的二狗子和伙伴,从藏身的大石包后面跳出来,摸到人群中蹭吃了。
就在二狗子和同伴蠢蠢欲动的时候,阿呷身下的柴火堆被点燃了。异常妖艳的火焰瞬间吞噬掉阿呷身上的擦耳瓦,接着就是整个身子。二狗子和伙伴见状不由吓呆住,几乎就在同时,原本平静的人群突然一阵骚动,一个女人挥舞着双手,就要想往火堆里冲。
“那不是阿伽吗?”胆小的伙伴不由拽了拽二狗子,二狗子肯定的点了点头,然后傻愣愣的继续盯着场中,没有离开的意思。后来,几乎所有二狗子的小伙伴都承认,当时脚莫名瘫软,根本迈不开步。
阿伽扑腾了一会儿,就意识到徒劳。于是,不再闹腾呆坐下来木木盯着燃烧的阿呷。时间过得很快,时间又似乎很漫长。所有人都围着大铁锅享受盛餐去了。头人一直静静坐在那里,身边放着最先捞出的上好牛肉也不吃,眼帘半垂,不知道心里在想些什么。
呆呆望着即将燃尽火堆的阿伽,掉魂一样,没有了刚才的冲动,这样的阿伽让头人放心。
然而,就在头人垂下眼帘的一刻,宁静坐着的阿伽突然发了疯般站起来,直冲水边。她的长辫早已经散开,披散的长发在身后几乎成了一条直线,这足以说明她的速度究竟有多快。快到所有人都猝不及防,快到当她挥舞的双手已快被大渡河流水淹没时,人们才慌乱奔向水边…….
一切就在瞬间,阿伽已经随着滚滚大渡河水向东流去。
秋天大渡河的水是那样的清,碧绿碧绿的水才能洗静阿伽身上的斑斑血痕。
秋天大渡河的水是那样的柔,轻柔温暖的水才能抚平阿伽心里的无尽伤痛。
河边火葬的是她的爱人,河水埋葬的是他的爱人。两个相爱的人,此刻总算能够永远相守…….
12
三十年后的某一天,两个肤色偏黑的中年男子,开着小车来到大渡河边的这个小村庄。下车后,他们从车上搀扶下一位头发花百的婆婆。
在婆婆的带领下,他们步履沉重的寻到当年这片河石滩。
年过花甲的桂婶子正和老伴在河边乘凉,当婆婆带着两名中年男子点燃祭品的时候,桂婶子迟疑着捅了捅身边的老伴:“老头子,你看那人是不是当年的阿美?”
是阿美,当年,阿美带着阿呷和阿伽的两个儿子逃出后,没有敢回山寨,而是在另一个汉人聚居地重新开始了生活。
阿美终身未嫁,为了姐姐的两个儿子打短工、做小生意,还真实现了阿呷当年的梦想,将两个孩子一起送到学校念书。
如今,两个孩子,大的新当选为彝人自治乡的乡长,小的自己做起了生意,一家人的日子圆满幸福。
..........
“阿伽,你可以瞑目了……”桂婶子望着河边缭缭升腾的青烟,口中喃喃念着……
岁月如梭,青山流水依旧。大渡河边的这个小村庄,越来越多的彝人迁居或借居于此,但他们之中早已没有砍山汉——退耕还林让砍山这个职业退出了历史的舞台。
当然,彝人越来越开明的婚嫁习俗下,也不会再有让桂婶子揪心的阿呷和阿伽……..
……...
——曼青2015年3月12日宝兴灵关修改3稿
个人简介:廖庆兰,女,1980年出生,四川省雅安市石棉县人。网名:俯身是尘,笔名:曼青,QQ:893709914。四川省作协会员,雅安市作协副秘书长。2002年开始在报纸副刊发表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2008年开始小说创作。2011年短篇小说《无处栖居》发表于四川《青年作家》。2012年短篇小说《一路公交》发表于《四川文学》。2014年6月,中篇小说《苍茫大地》发表于《四川文学》。2015年4月,中篇小说《镐刨》发表于《四川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