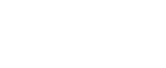龙江坳
小时候,家住夯补市,特贪玩,常缠着母亲,软磨硬泡地要她带我去邻县的夯沙乡去赶场,慈母爱子,确实想满足我的愿望,但又怕因此耽误了我的学业。于是,弯下腰,拍拍我的小脑袋,顺手指着对面的大青山说:“满儿,去赶夯沙场是要爬坡的,你还小,爬得起龙江坳吗?”
龙江坳,又名“杀人坳”,当地的苗民则叫它“扎高惹”。属吉首辖地,位置在吉首市北,是个一脚踏两县的地方。因为到了坳顶,再往前一步,就是保靖县的领地了。去龙江坳,要从吉首市五里牌屠宰场出发,坐车,沿小溪河一路北行,大约四十里样子,来到一座大青山下,再走,绕上一大段盘山路,爬上一座高坡,坡顶便是。
最初,它是因为坳旁的龙江村而得名。但自大清王朝以来,百余年的时间里。湘西这个地方,民不聊生,匪祸不断,而且,官府还有规定,犯了王法的人,过界无事。因为过境抓人,是大清法律所不允许的。所以,龙江坳特殊的地理位置的价值,得到了凸现,常常有大股土匪,在不确切的时间里,出没于龙江坳。他们仗着人多,势众,有枪,便在龙江坳上抢光洋,抢物,抢大烟。受害者稍有不从,或者表示认识其中某某土匪,便招来杀身之祸。或一刀,或一枪,就使受害者一命归西。然后,随手一推,那尸体,便“窸窸窣窣”地顺着山坳滚下去,或腐,或烂,也就无人过问。所以,附近的苗民往往是谈起龙江坳,就有些心惊胆战,称龙江坳是“杀人坳”。
当然,历史和生活不可能总是在一种满满的压抑下,负荷前行的,土匪,是特定历史环境下的一种产物,邪不压正,才是真理。生活在龙江坳附近的乡民,对龙江坳抱着一种特别的爱。尤其是那些花花绿绿的少男少女,总是相约着,或赶场的时候,或晚上,去龙江坳唱苗歌,谈情说爱,去挑选意中人。他们认为,去了龙江坳,一定能够找到那么一个漂亮的,聪明的,能说会道的人,做自己的终身伴侣。这样,龙江坳就成了那些想充分展现自己聪明才智的年轻人的一个重要场所。被称为“扎高惹”,“扎高”,在苗语里是“山坳”的意思,“惹”则表示“聪明”。
夯沙属于保靖县,是场,古历逢五逢十赶场。附近的乡民,总是把自己的土特产如土茯苓,金银花,五倍子或者桐油、茶油、鸡蛋什么的,拿到夯沙去卖,然后,买上一些布匹,煤油,盐,锅子,碗,坛坛罐罐等等,日常用品回家。土特产的最后去处是所里(吉首),日常用品的来源也是所里,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还不通车,所以,从所里到夯沙,实际上是一条商道,相当于古时中国的西北通往西亚的那条“丝绸之路”。那些忙碌的商人,挑夫,僧侣,以及夯补市河以下的赶场人,总是络绎不绝地出现在这条路上,龙江坳,是个休息的点,相当于“丝绸之路”的驿站。
清末民初,夯沙的杨氏家族很有钱,他们出于积善行德的本意,花了一些银两,在龙江坳上修了一座亭子,供来往的行人和坳旁劳作的乡民休息,避雨,亭子有三间木房子那么大,盖瓦的,挺气派,为了防蛀,还涂了桐油。那时候的龙江坳,因为有了这亭子,着实风光了好些年,只是可惜,由于年久失修,无人管理,亭子在岁月的风雨飘摇中倒塌,最后慢慢地消失了。
它的东方是山,西方是山,北方是山,南方还是山。山坳上,有百来米不规则的石板路,弯弯曲曲的像醉鬼走路一样,穿坳而过。路的两边,有许许多多奇形怪状的石头,有的像人,有的像鬼,有的像家具。那时候,我还小,有时候是因为赶场,有时候是因为放牛,有时候是因为玩耍和放风筝。常常坐在龙江坳上,用好奇的眼光看着这些石头,真担心从某个石头缝里面蹦出一个能翻跟斗的孙悟空,或者什么九妖十八怪来。村里的龙把果老爷爷,还指着一块大石头忽悠我说:“老满,看到那块大石头了没有,它以前睡过一个神仙,这个神仙的名字叫吕洞宾,他在这里睡了整整九九八百一十年,醒来以后,往北走,因为惦记着这里的山石风光,竟然不由自主地往回看了一看,这一看,便失去了仙气,立马化仙身为山石,变成了一座山,后人叫它“吕洞山”,你呀,以后不管做什么事,一定要一心一意,可不要像吕洞宾那样,东张西望的,白白浪费了仙气。”
吕洞宾由神仙变石头的事情,我无法考证,肯定是无稽之谈。但是,那时候,我常常看见有很多带枪的民兵,在龙江坳上盘查行人。他们问过路的人要证明,要路条,还检查他们身上的行李。据说是因为当时阶级斗争非常复杂,这样做,可以防止阶级敌人的破坏活动。我还记得1972年的时候,上面来了政策,说是为了反贪污,反盗窃,反投机倒把,反铺张浪费。粮食不准自由买卖,违者必究。但是,那些急需要钱的,急需要买粮食的乡民,在龙江坳相遇了,也就悄悄地就地成交。
有一年,龙江村的一位八十四岁的老伯伯死了,村里的男女老少都去帮忙。女人们帮着洗菜,煮饭,男人们的主要任务是抬丧,墓地选在龙江坳旁的一处小山坡上。到了出殡那天,死者家属们披麻戴孝,哭哭啼啼的,伤心极了,而村民们则忙着帮放鞭炮,抬花圈,吹吹打打,显得很是热闹。大家吆喝着,推推揉揉,走走停停,把死者轰轰烈烈地抬上了山,埋了。不过,后来,死者家属没有办法,又请人把那些抬丧的人,一个个地抬了回来,一共抬了十八个小伙子。因为,乡下埋死人,有闹酒的习惯,小伙子们要吃糖,要喝酒,主家不得怠慢,直到最后,抬丧的人,自己喝得酩酊大醉,横七竖八地躺在墓地旁,不省人事……
1977年,我十三岁,懵懵懂懂的心智,也开始知道了一些甲乙丙丁,天干地支来。有时候也会背着老师,跟着村里的一些年轻人,做出一些荒唐事。邻近的夯达会村,排几绒村,平年村等等那些年轻的姑娘们,常常利用晚上,相约到龙江坳来,与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唱苗歌,说笑话。我去了几回,觉得好玩,比读书有味道多了。
皓月当空,月亮亮得发白,她们来了。说好了的,是八个姑娘对八个小伙子。但是因为村里的小伙子临时凑不够数,十三岁的我,便加入了他们的行列,作为计划外安排。当然,对方也会安排另一个计划外的姑娘,与我聊天。
她圆脸,大眼睛,包着方方正正的苗帕,说话的声音清脆得像个播音员,笑的时候,还有两个酒窝窝。她在龙江坳上走来走去。山风吹过,山雨洗过的石头,本来就很干净。但她仍然不放心,她把自己的围裙解了下来,铺在石头上,让我坐,随后,她又去附近的草丛中,找来了一些“救兵粮”给我吃,那“救兵粮”是一种野果,红彤彤的,像微型苹果,味稍酸,树枝还带刺。
她告诉我,她今年二十六岁,在家里织布,绣花,有时候还打猪草。家里什么都有,就是……缺少一个小弟弟。她问我:“你会唱山歌吗?”我说:“不会,在学校老师不教我们唱山歌,老师只教我们唱一些电影歌曲。”她说:“电影歌曲在龙江坳是没有用的,因为电影歌曲是死的,变化不了,而山歌是活的,想怎么唱就怎么唱。你想想,死板的歌曲,怎么能够表达活生生的爱情呢?不过,也没关系,你要是肯天天到龙江坳来玩,我可以教你。”我说:“我很笨,学习成绩不好,经常考试不及格,学唱山歌,怕是学不会的。”她说:“不,你挺聪明的,看你这鼻子,这眉毛,这眼睛,很有灵气。我敢肯定,你一学就会,一会就精,将来,一定是个‘巴甲沙’(苗语:山歌手)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我有点尴尬,我说:“我姓杨,村里人都叫我老满,那么,大姐姐,你姓什么,叫什么名字?”她有点眉飞色舞了,偏着头,仔细地看了看我,说:“我呀,我姓龙,名字……你就叫我龙江坳吧。”
我觉得她在打马虎眼,哪有叫龙江坳的,这分明是在忽悠我。刚想和她狡辩一下,她却很快地把“救兵粮”递了过来。她说:“吃吧,吃吧,这果子野生野长,自生自灭,是顺其自然的命,吃起来,有一股……家乡的味道。”我只好把手伸出去接“救兵粮”,但“救兵粮”有刺,我不小心,刺得我手指出了血,好痛好痛。我飞快地想把手缩回来,却无意中触碰她的胸脯。顿时,我的脸红了,目瞪口呆了,我估计是闯了大祸。但她却很羞涩地咬紧牙关,忍住了即将爆发的笑。
她问我:“救兵粮好吃吗?”
我说:“好吃,大姐姐的救兵粮很好吃。”
她又问我:“大姐姐的围裙坐起来,舒服吗?”
我说:“舒服,很舒服的。”
她又说:“你觉得大姐姐漂亮吗?”
我说:“漂亮,像仙女一样,真的很漂亮”
她又说:“那么,你喜欢大姐姐吗?”
我说:“喜欢”
最后一个问题了:“既然大姐姐漂亮,你又喜欢大姐姐,那么,你可以娶大姐姐做婆娘吗?大姐姐晚上可以和你一起睡觉。”
我懵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我只好说:“这……这……这怎么行呢?大姐姐,我还没想好,我娘会打我的,我不敢……”
这下可把她惹气了,她站起来,先是刮了我的鼻子,然后是提了我的耳朵,还高声吼了起来:“你这个胆小鬼,你这个窝囊废,你这个无情无义的家伙,你这个口是心非的东西,刚才,还说我漂亮,还说喜欢我,却原来是,吃了我的救兵粮,坐了我的围裙,还摸了我的奶子,才一转眼的功夫,就不要我了?不行,我跟你没完……”
我觉得,人生是短暂的,就像一年之中的春夏秋冬,就那么一季。花开花落,也是临时的,就那么一闪一现。但总是有些人,有些地方,有些事情,在你的一生中留下一些痕迹,让你永远忘记不了。尤其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不但不淡化,反而慢慢地更加清晰起来。这样,当你觉得它,站在你记忆的某处,微笑着向你招手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它的温暖,言谈举止之间,你会不由自主地向人表露一番,因为你不想辜负它,“不吐不快”。
写“龙江坳”,是想让自己更加接近它,不让它变成为我的“边缘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