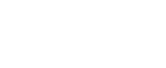小说课堂张炜小说八讲之 故事 (5000字)
小说课堂张炜小说八讲之|故事
2014-08-18张炜小说选刊
小说课堂|张炜小说八讲之|故事
文/张炜
传统和现代
上一讲我们讲了“语言”,这一讲讲“故事”。平时一谈到小说,有人首先想到的就是它讲了什么故事——在很多时候,不少人真的是把读小说等同于看故事的。可见故事在小说中占有多么突出的位置。
其实“小说”和“故事”仍然是不同的,“小说”里肯定有“故事”,但仅仅有了“故事”还算不得“小说”。
初学写作者往往不自觉地把“故事”和“小说”等同起来,一开始可能只想怎样编出一个好看的、吸引人的故事。有较长写作经历的人,比如现在的小说家们,想得比较多的是“我怎么讲这个故事”,想让小说在讲法上出新。还有写作课老师,也要教授讲述技巧。作家认为不同的讲法是非常重要的——这体现了自己的个性和文学价值。
可是作为普通读者,他们只要看好看和有趣的故事,不会过分在意故事的讲法。从“讲法”上着眼,这更多的是作家的事情。一般读者与其说要欣赏一部文学作品的结构艺术,还不如说想看一个好故事。
不过在作家和文学研究者眼里,同样的故事由于有了不同的讲法,书的品质肯定会不一样的。讲述方式不同,书的结构就不同。所以我们也可以说,分析故事大致也等于分析小说的结构了。一部书从大的方面看,里面发生的故事总是有开头有结尾,中间经过了发展变化——可是到底怎么组合、怎么讲述,学问就大了。
现代作家讲故事的方法千变万化,已经远离了习惯和传统。就我读过的书来说,印象深刻的有这样几种:一是按时间顺序从头讲叙的,这是比较常见的,读者容易集中精力看下去。我们最熟悉的中国传统小说中,常说的有两句话:一是“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意思是话题要岔开一点了,先给读者(听书人)提个醒;再一句话就是“且听下回分解”,告诉读者不要离开,下边还要接上说的。可见那时的小说讲起故事来是非常老实的。二是到了现代,因为小说主要是供人纸上阅读,而不是“听书”,这种纯粹的写作活动使讲述进一步走向了复杂化——它成为一种文字实验,写故事可以不按时间顺序,想从哪里开始就从哪里开始,有时还交织进另一些不同的故事。
现代小说写作怎样脱离了传统的故事讲述,我们可以试着分析几种,但要全部历数一遍也不可能。
随着小说的“现代化”,进入二十世纪以后,作家们在语言上创新求变,在故事上更是如此。因为不这样就无法超越以往的经典。经过了各种尝试,起码可以说在叙述方式上以往那些大师没有做过。这对文学的发展当然是重要的。
我们平时所说的“故事”,包含了情节和细节两个方面。情节就是大的故事脉络,即人物之间有着怎样的矛盾和冲突,高潮低潮,转折起伏,直到结局——总而言之是一个相互衔接的链条。但是这个链条要由一些更小的环扣组成,在写作学里把它叫做“细节”,即含在情节里面的小构件。我们从汉字的组合上也可以去感悟什么是“情节”:情,情趣、情境、情怀;节,环节、节段。
通俗文学中的故事讲述,一般不会打乱时间顺序,尽量不让读者游离和走神。但现代纯文学(雅文学)是一种诗性写作,在故事的讲述方面就走得更远——而在传统小说中,雅文学与俗文学在讲法上并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
让我们来看看传统小说,比如《红楼梦》,它是最典型的纯文学。四大名著中,像《西游记》《三国演义》和《水浒》,大致要归属到民间文学里去,因为它不是由一个作家创作出来的,而是经过了许多人的口耳相传,到了文人那里再整理出来。这种整理有再创造的部分,但主要还是依赖无数人的创造成果。
很多人曾把“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混淆,因为前者也具有通俗性和娱乐性。但仔细分析,民间文学从本质上看仍然还不是通俗文学——它经过了那么多人的修改和创造,无论就人物塑造还是语言艺术来讲,都变得极其丰满和成熟,有了充盈的诗性,文学含量很高,已经是远非一己之力所能达到的境界。所以我们常常把“民间文学”和“通俗文学”加以区分,作为两个不同的品种去对待。
但无论雅俗,传统小说中的故事大致都是线性的、按时间顺序发展的:环环相扣,有时候虽然也会荡开一点,但不同的线索很快又会合而为一。它的整个故事没有过分复杂的结构关系,所以在阅读时不必费很多脑筋去捕捉头绪,用不着在头脑里把不同的故事板块重新组装。在这方面,国外国内大致都差不多。
到了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就不同了,在“纯文学”这个范畴里,讲故事的方法和通俗文学大幅度地拉开了距离——相当多的书在一般读者看来已经“不再正经地讲故事”了,它们声东击西,言不由衷,有时候还故意把一个完整的故事拆得七零八落;有时把不知多少个故事掺在一块儿,看得人头昏眼花。最后,这样的故事专业人士也看不懂了。
专家们研究的某些现代小说,离普通读者的确是很远的,它们真的需要一批专业人士来读。受这样倾向的影响,纯文学的阅读范围比以前大大变窄了。这是不必讳言的。
十九世纪或以前的作家用传统方法讲故事,写出了很难超越的杰作。这成为作家的难题,他们没有办法,就给读者出起了难题。这样做的不良后果其实十分严重,代价也很大。
但是如果认为只要是“现代派”,就一定是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讲述方式,一定是打乱时间顺序的,那也是一种误解。现代小说中,按照时间顺序讲述的仍然很多——但即便是这种讲述,也在内部藏下了许多诡谲——它可能在叙述的节奏方面、在情节与细节的关系方面做了许多手脚。它的气质已经发生了改变。没有办法,现代主义的水流一旦开始了,也就没法回头、没法回到真正的传统上去了。
同时呈现的故事
说到现代小说的结构,先让我们以博尔赫斯为例:他是阿根廷的一位小说家,曾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被中国作家津津乐道。他是短篇名手,被人尊称为“作家们的作家”,技高一等。他的小说结构就像“迷宫”,故事幻象丛生,与传统的阅读经验相去很远。关于他的讲述技巧的分析,在西方文学著作里很多,影响了很多作家。
一般说来我们写一个短篇,不太主张把情节搞得太过纠缠。比如正讲一个故事,突然又开辟了另一个故事?或制造出新的悬念,这样一来,读者跟着作家的笔游来弋去,难免会糊里糊涂的。在五六千字或万把字的篇幅里,出现这么多的线索和头绪当然是犯忌的。可是在现代主义作家那里,有时却是刻意为之的。他们的很多作品可能并没有想过写给谁的问题,而是热衷于一种实验、一种智力游戏。在这方面博尔赫斯走得很远,具有了范本的意义。
这种范本的真正价值在哪里?这就好比服装展览,模特儿们在台上表演时穿的那些服装,一般来说是不宜直接搬到生活中、不宜穿到大街上的。可是这种活动却可以提高我们的服饰艺术,对我们的实用服装的式样变革起到推动作用?它提高我们现实生活中的想象力,让我们的创造变得更大胆更有活力。
现代主义小说的勇敢实验,的确从总体上推动和强化了文学的表现力,这个不容否定。仅就故事的讲述这一项,它的效果和作用也是明显和巨大的。中国作家现实主义根脉扎得又深又牢,每个地区都有自己土生土长的作家,但就连他们也在变化,讲故事的方法不再那么守旧和传统了。而文学形式上一旦变化,可能其他方面都连带着打开了,让人觉得面貌一新。
除了博尔赫斯,人们一度谈得比较多的,还有意大利的卡尔维诺、拉美的略萨和科塔萨尔等一长串名单。略萨常常被称为“结构现实主义”,讲故事的方式有些特别:开头讲述时会让读者用传统的眼光打量,但发展下去就令人觉得怪异了。他的书刚刚译到中国大陆时让人称奇,时间一长,读者对这一套方法倒也熟稔了、习惯了。这当年在许多人眼里被看做现代小说结构的入门书,因为比较起来还算简单一些、有规律一些,容易把握。他通常用镶嵌的方式,将几个不同的故事在书中同时呈现出来。
如《胡利娅姨妈与作家》这部长篇小说,它的开头讲主人公“我”怎样爱上了自己的姨妈——这种有违常理的事情自然要遭到百般阻挠,结果“我”为了结婚跑来逃去,本身就是个曲折有趣的故事。显然,这个骨干故事足以吊起人的胃口:违背伦常、年纪相差悬殊、与家族内的斗智、一场激烈逃亡、逃到一个地方去结婚、说不完的麻烦、最后终于如愿以偿??
它讲述了一个十八岁的小伙子爱上了一个不该爱的三十五六岁的女人,故事本身包含许多撩拨人的元素。这都是好料。就凭这些,作家在讲述时十分自信地荡开去,将主要的线索中断了,转而去讲别的。
其实越是波澜起伏的故事,越是留下了做手脚的余地。“结构现实主义”有一个特征:读者刚开始顺着它的情节往前走的时候,另一个故事板块就硬生生地插了进来。这次略萨让一个电台主持人登场了,这人个子矮小,怪异——他彬彬有礼,越是庄重越是逗人发笑。他在电台里主持一个节目,内容耸人听闻,像是一些独立的短篇。结果这个节目的讲述就构成了小说的二重奏,开辟了另一个饶有趣味的场景。这第二个板块里面有各种奇闻逸事,同样起伏跌宕。这诸多故事一起呈现,读者被吸引的同时又要张望环顾,阅读效果变得奇妙:寻找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并依据自己的生活经验和艺术经验加以组合,从而获取非同寻常的快感。
这与我们的传统小说差异很大。它的几个故事板块当然不是简单地镶嵌,还要有些照应,有些连粘点、焊接点。尽管这样,这部小说还是有许多同时进行的故事,它的枝蔓和穿插不但没有使全书解体和垮掉,而且能让读者津津有味地读下去,这就是作家的本事了。
这位作家还有几部小说,结构方式大致如此,如《绿房子》《潘达列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世界末日之战》等。书中展开的几个故事之间一开始是没有关系的,都在作家给出的一个空间里同时呈现,往前平行推进。它们形式怪异,所讲述的内容却是十分现实的——虽有联想意识流等手法的运用,却没有什么触目的变形手法,这方面不像卡夫卡也不像马尔克斯。它仅仅是以特别的结构为标志,于是就被称之为“结构现实主义”。这是理论家们的概括,我们也暂且这样叫着。 很多的现代主义小说都沿用了类似的方法,不同的是有的还要加上神话或魔幻之类,那就更复杂一点。让不同的故事交织和呈现,这和我们传统小说的穿插回忆、倒叙等等还是有极大区别的。传统小说里也可以有小的故事板块,它最后总要衔接到大故事上,与之形成一个整体。而现代小说中这些不同的故事,其地位往往是接近或等同的。
今天小说的讲述方法已经千奇百怪,难以划分类型。比如说一部叫《跳房子》的小说,也是拉美的,作者是科塔萨尔。它的讲述顺序更自由更随意,读者可以从小说的随便哪个部分看起,也可以从头往下看,以此来激发出每个阅读者编织故事的能力。从不同的部位看起,最后组合的情节是不一样的,感受也不一样。再如塞尔维亚的帕维奇,他的《哈扎尔词典》是以词条的方式结构的,据作者说读者可以像查字典一样读他的书——这种阅读的效果如何,我还没有很深的体验。有一点是要肯定的,就是作家的想象力、他在文本结构方面的大胆和自由。
这方面的代表性作品很多,比如更早一些的,就是美国福克纳的名篇《喧哗与骚动》,它的第一章从一个白痴的视角去叙述,这样故事就显得“稀奇古怪”:零散的拼接、穿插、重复,一切都成了顺理成章。读者就在这种怪异中品咂出特殊的阅读快感,而这种故事是无法传统的——好在作家给了我们一个逻辑、一个理由,就是让我们事先知道这是傻子的眼光。可是到了卡夫卡或马尔克斯那儿,已经完全不需要这样的理由了。作家获得了进一步的解放,手中的故事怎样摆弄都可以了。马尔克斯看了《变形记》以后,就说了一句俏皮话——这句话被大陆上的作家重复了许多遍,我却不太相信是马尔克斯的由衷之言——“妈的,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
他说的是自己获得了一种叙述自由,说的是解放后的快感。这里面多少能让人嗅到一点夸张的气味。他的“解放”和“自由”当然不会是因为看了一部现代小说就发生了突变。
还有更复杂的叙述——
一个大故事里面套一个小故事,小故事里面还有一个更小的故事,被称为“东方套盒”“俄罗斯套娃”式。比如说阿特伍德,加拿大女作家,她有一部长篇叫《盲刺客》,就采取了这种方式。这种讲故事的方法在现代小说里越来越多,实际上并没有多少难度——关键是当作家运用这种方法的时候,能在多大程度上与内容紧密结合。这才是最难的。单纯玩弄“方法”的人不少,这只能迷人一时。
俗话说“戏法人人会变,手法各有不同”,关键还得看手段高低。现代主义小说如果只在形式上闹出千奇百怪,那也太廉价了。当然不会这样。它总的根源还要扎在当代生活的土壤里,也就是平常说的那句话:“内容决定形式”。仅仅为形式所累,那可能只是创作走入枯竭的一个征兆。
小说的两种节奏
虽然都是讲故事,雅文学和俗文学有完全不同的讲法。如上说的那些现代方法,一些千奇百怪的试验,俗文学可不可以使用?很难回答。通俗小说或许也可以吸收一点现代小说的讲述方法,但不会是主要的。一般来说它不允许破坏原有的线性结构,不允许随意镶嵌和跳跃——运用“东方套盒”“意识流”?这样的玩笑开不得,这会失去大多数读者的;没了大众读者,没了广大民众的“喜闻乐见”,通俗文学的生存基础就抽掉了。有人会说:通俗小说讲故事要求快节奏。
是的,但从另一个方面来看,雅文学要求讲故事的节奏更快——也正是因为这个“快”字,它才成了雅文学。有人可能会说,你弄反了吧,雅文学是慢的,通俗小说才快,比如看武侠和言情小说,它的故事曲折多变,稍微一慢就读不下去了。
那就让我们分析一下吧。
我们前面说过,故事当中起码包含了“情节”和“细节”,而“情节”是要依赖“细节”的。没有“情节”不走,没有“细节”不圆,它们相互补充着才能把故事讲下去。一般说“情节”是容易叙述的,它很外向;“细节”得有描述的功夫,它比较内向。故事在小说里其实是表现为不同的两种节奏:两种节奏在书中并不一致。我们不能说一本书的“情节”快了,它的“细节”就一定快了——有时还正好相反。
以通俗小说为例,拿出一本小说来看,一两个印刷页面里的故事转折——也就是所谓的“情节”,平均能发生一次也就差不多了。所以说这样的书可以读得很快,快读并不会漏掉什么,因为我们关注的只是“情节”——慢了完全不必要。一两个印刷页的文字才有一处大的情节转折,所以从文字行走的速度上看,真的是太慢了。读者不得不快些翻阅,因为实在不愿顺着缓慢的文字往前读。这种文字的慢节奏,是显而易见的。
可是如果打开一部杰出的纯文学作品,比如《红楼梦》,每一处文字几乎都不愿让人放弃,这是语言和细节吸引人,是它有意思。它的文字在行走的节奏上是快的,阅读时要紧紧跟住,无法往前急赶。我们这里说“细节”也许不准确,而应该说“细部”,因为吸引我们、调度小说节奏的,不光是细节,还有语言本身,有说话的方式等等。
还有一个好例子是索尔·贝娄的小说,比较一下他的作品,就更加明白这个道理了。《洪堡的礼物》四五十万字,很厚的一本书了,可是只写了几天的事情。但我们会一直被它所吸引,这吸引力不是来自曲折的大情节,而是细部、是语言,是局部的转化特别频繁——大概在一个印刷页里就有四五处足以吸引你的地方。如果没有那么多细节的摆渡,大的情节转折就会显得空洞苍白。在细部,在局部,它特别密致、刺激,转换灵快。
比如说通俗文学吧,它在走向情节转折的时候并不需要更多的细节,也不需要吸引人的局部,只为一个大故事负责。在语言叙述方面,句子也比较平直。那些武侠小说、言情小说和社会批判小说,语言大致是这样的。这不是因为作家的叙述能力不够,而是讲故事的方式决定了必须要采用较为平直的语言——如果叙述语言不停地跳跃,读者就要不断地调动感悟力和人生经验去重新组合拼接,去玩味语言和细节,对情节的注意力也就被转移了——这并不是作者的目的,不是他希望看到的。
同样的道理也在公文写作中体现出来。比如说机关里的文件,就不能用过多含蓄的、幽默的语言去描述,而只能使用特别规范的常见语,词汇太生僻、太深奥都不适宜。但文学作品的含义有时要模糊,不能太直白,要给读者留下想象的空间;公文就不同了,一是一,二是二,必须表述清楚。这种语言应该是直线的,不能是曲折跳跃的。它使用的词汇必须是大家都熟悉的,知道它的内涵外延,概念要准确。于是我们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作家们使用的语言,一些新的词汇和造句方式,大约要停一两年抵达新闻媒体那里,再过三五年甚至再长一点时间,才可以运用到公文中去。词汇周转运动的轨迹大致是有规律的:从作家那里起步,最后回到公文——在新闻媒体和公文之间还有一个环节,就是民众,要在民众当中使用一段之后,才用到公文里。所以说,一个时期有一个时期的语言套路,这个套路最开始的时候还是出自作家,那是创造源。有人说群众才是创造源啊,当然,但从提炼和形成、一直到运用,还是需要作家。
一般来说,大的情节转换是外部的直观的,所以我们用不多的语言就可以讲得清一本书写了什么故事。而细节和局部就复杂了,它很内向,我们几乎难以复述。可见一本书同时具有两个节奏:不妨叫做“内节奏”和“外节奏”。从这个意义上说,通俗小说的“外节奏”是快的,即平常意义上的那个“故事”是快的;可是它的另一些东西是慢的,那些细部和局部里的东西——语言调度、细节频率——是慢的。纯文学小说正好跟它相反,它外部的直观故事比较简单,一点都不复杂,有时候几句话就可以讲得清楚;但是它的细部、细节调整得很快,也就是说,它的“内节奏”是快的。如果一部纯文学作品的“外节奏”太快,超过了一定的速度,一定会损害它的品质。
刚才说的《洪堡的礼物》里只写了几天的事情:好朋友怎样出名、怎样疯掉,“我”怎样后悔内疚??故事十分“简单”。但里面穿插的一些小故事、一些细节让人眼花缭乱,不能挪动眼睛,恨不得每个字每个词都盯住,看得过瘾。总之读者被紧紧地吸引住了。讲到“故事”,从大的方面看世界上也就那么几个类型,无论编得怎样巧妙,无非就是生老病死、欺骗、忠诚、爱与伤害这些东西。但是“故事”的褶缝里,各种千奇百怪的、让人想象不到的、人性中最偏僻的角落里藏匿的那些细节,却是永远也说不尽的。
归总来看,衡量一个纯文学作家讲故事的能力,更多的不是看“外节奏”,而是看他的“内节奏”。——越快越有难度,也越吸引人,作品也就越杰出。
被一再压缩的“故事”
一般来说,小说家必然是讲故事的高手,不会讲故事,还怎么写小说?可见这是个常识。不过也就是这种“常识”让不少写作者产生了误解。对于“故事”及其意义,纯文学作家与通俗作家的理解和要求是不同的。都在讲故事,讲法上差异很大——通俗小说是属于曲艺范畴的,主要功能是娱乐,虽然也“寓教于乐”。它需要群众的“喜闻乐见”。而纯文学就不是这样,它主要还不是娱乐。如果一部纯文学作品一味强调群众的“喜闻乐见”,那就糟了。
历史上的文学名著,百分之九十以上不是一出世就让群众“喜闻乐见”的。杰作总是留给了时间,它在获取读者的数量上一定需要相应的时间才行。不用说一些极端的例子如《尤利西斯》《追忆逝水年华》《没有个性的人》之类,就是《红楼梦》和鲁迅的书,在问世之初也不会风行吧。
现代小说越来越不追求“故事”的膨胀,相反倒是不断地压缩它。而它的细节、细部却在扩张。大的情节转换时,只简单交代一下——好比从一个部门到另一个部门去报到,开封介绍信办个手续就行了,到岗之后就得一件件处理具体的事务了,要求真求细。这又像一个大口袋,里面装满了东西——那些精彩的细节就像一颗颗宝石和珍珠,装成了一个个大袋子。这些袋子怎么办?就放在那儿?这当然不行。结果作家就做了许多“钩子”,把这些袋子连到了一起。“钩子”相连接的部位就是“情节”,可见它已经给压缩成了这么简洁。而通俗小说好比一条从头至尾环环相扣的锁链,匀称、漫长,阅读就是顺着这条锁链摸下去。
现代小说开始的时候,某些作家只是将通俗文学的“链子”截得短一些,并且时不时地停下来,开拓和经营出一个个空间,在里面塞上一些精美的宝物,好像金银细软一类。后来这种金银细软多了,仅有的几个空间放不下了,于是就进一步想出办法:做成一只只大口袋,把许多好东西都装到里面,最后只把口袋用情节的“环子”和“钩子”连起来。不连起来不行,那就没有情节了,也就不再是小说了。所以说像库切这样的“口袋大家”,最后还是要将不同的“口袋”连接起来,因为他写的是“长篇小说”。他的一个个大“口袋”里,我们得知一些装了“理论”、一些装了“感想”、一些装了“情趣”和“爱欲”之类。他还有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为这些“口袋”建了不同的仓库,垒了围墙(在页面上画出两道直线),将不同的“口袋”贮存在里面。
上期讲的《哈扎尔词典》和《跳房子》,一堆环扣、一个个“口袋”就摊在地上,让读者自己去随意连接。这或许有些麻烦,可是世上的读者是千差万别的,有人可能愿意这样做。
《红楼梦》与一些言情、武侠小说不同的,就是大的故事(情节)被压缩了,而装精美细节所需要的大“口袋”准备了不少。越是杰出的作家,这种“口袋”越是结实、越是大——小了盛不下东西,不结实就会被撑破。
还有“钩子”和“环扣”,更是需要结实,因为不结实就会被折断。所以到了现代,作家们使用的材料就更是先进,让强度大大提高。作家的基本构筑材料是语言——超强的语言能力被视为成功的首要条件。一般的语言能力无法经营出一部现代杰作,因为现代建筑对材质有个基本的承重要求——越是大的重量负荷,越是需要超强的材料。
现代小说与传统小说相比,对作家语言文字水准的要求已经变得空前严苛。小说家当然是故事大家,但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讲故事——它首先要求作家是一个“宝石”和“珍珠”的收藏家,就是说,作家要具备调度语言和描绘细节等方面的高超能力。
来源:《青年文学》杂志
*** *** ***
《小说选刊》中国作协主管,中国作家出版集团主办,各地报摊均有零售。邮局订阅,请报邮发代号:2-210,定价每期10元。
欢迎新老朋友关注《小说选刊》微信平台,如觉内容不错,请扩散至朋友圈。
《小说选刊》微信公众平台,微信号:XSXKZZ
扫一扫二维码,也可关注《小说选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