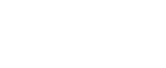水格(七)
146、出世美学
滚滚江河,浩浩东归。九派百脉,节节生枝,像一棵巨树,覆荫着中国大陆。日夜在流淌,日夜在生长。或则静穆,渟渟脉脉,涵泳万物;或则浩荡,惊天动地,慷慨激越;或则明净,千里澄清,晶莹纯洁;或则重浊,洪流翻卷,悲壮苍凉。如此一路奔涌而去,一路激荡着地上人们的心灵,陶冶着他们的性情,模塑着他们的性格,而不特养育他们的生命,并且养育他们的灵魂,使得此不灭的灵魂铸成自己的感应方式,而成为中国文化所特有的感应方式,并以这一套方式接应着这个世界,接应着自身所在的人群,而在永恒流变之中,为灵魂安顿了一个足可安身立命的家园,避免了灵魂的流浪无定。
这时候,当他们再看那来自“天外”的黄河,那奔向“天外”的长江,而深切地感受到这与人生命运似乎同一格式的“来自天外,归向天外”的漂渺无常时,心灵没有了因无常而陷入彻底的虚无,彻底的彷徨无主,却在此无常之中充分吮吸到一种格外有滋味的美,一种明快中深含忧伤的美,一种重浊中深含期待的美,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文化美学律式的中国式的浑融的美,不可分析,却最使人心荡神移。
如果说,这长流不息的江河就是一道长长铺开的人生命运的驿路,那么,那挂在河江干流上的湖泽正成为这驿路上的一个个驿站,成为这长途旅行中疲倦的心灵所渴念到达的一个个店家。店家也是家,足可驻下脚来,长长喘上一口气,暂时离开那“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式的紧张要命的跋涉,而品尝一下那难得的人生一日之“闲”。在此决无争竞、决无污浊的五湖烟霞之中,吸风饮露,养气息心,即使片刻,也足慰平生了。而此湖此烟,也就成为了中国文化数千年不改的理想胜境,使得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心向往之,魂梦萦绕,即使身在庙堂,荣耀已足,依然放不下那颗要归野的江湖之心,如此,才算有神致,是大雅真美。
无论是雅是美,决不仅止于一种个人的私人爱好与追求,这种“出世美学”恰恰正是为社会所需要、为社会所造就和利用的一种“社会美学”。这就是,此远离人世之云水胜境,其所蕴含的那种冰清玉洁的品质,正回过头来为此一热闹扰攘的人世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参照,为人世中一颗颗跃动着的俗心凡心,供出一个值得效法的超凡入圣的榜样,而以此为价值参照之标尺,不断校正社会,引领社会,离开浊俗,向纯正靠拢。由此,前述那种中国文化“身在庙堂,心念江湖”的美学判断,于此恰好反一个个儿过来,成为:“身在江湖,心念魏阙。”关怀人世,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便成为了浩瀚的洞庭湖向社会发出的一份关于人生理想的宣言。
这高度美学化了的文化理想,是如此地打动人心,深入人心,以至以其不可遏止之猛势,随着中国历史的逐步展开,而向人世作了全面的渗透,引领人心对自然与社会开始最彻底的融和,将人世引入自然,将自然引入人世。
尘世之心与自然之心相浑融,带来的一个副产品,是产生了中国式的园林:一个将无边自然云水浓缩以后,搬放于人世中最热闹的地方——城市,以为供人栖息的心灵之家。这种中国文化中国用心的中国园林以“山水精神”为元神,而与西方园林那种人跳出自然、主宰自然的西方文化“雕塑精神”适形成对照。
中国文化的山水是有灵性的,有心,活的。山水精神就是人文精神,山水的心灵就是人的心灵。山水无言。由此中国园林发明了由人出面、人与山水共同宣言的“题额”精神,浩然、幽然苍秀林水,一题之后,妙境顿开,天地自然之精魂也便被收摄入园,浓聚天心,收摄人心,天心与人心彻底浑融归一;人心回归自然,自然入溶人心,达成一种至上之美境,再分不清天人的界限。当其时也,曾文正有言曰:“虽南面王不以易其乐也。”
这的确是一种高超精绝的艺术,一种中国文化关于宇宙人生的哲学美学,空前绝后。
147、美,不可拒绝
宇宙众生,依水立命。天下美景,水为灵魂。因为有了水,山得以青,花得以红,这个世界才有了生机,有了色彩,成为属人的世界,生的世界,美的世界。
《世说新语•言语》:“从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使人应接不暇。”
唐吴融《富春》诗:“水送山迎入富春,一川如画晚晴新。”
陆游《游山西村》诗:“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此种诱人醉人的美,都无不因了其中有“水”的点画和点化。
不错,水情时苦,所谓“苦雨成霖”,“苦海无边”;水情时忧,所谓“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李白)“谩夸书剑无好处,水远山长步步愁。(许浑)但是少有人知道,这苦与愁却原是喜与乐之变相,是喜乐之别一种形式,一如爱是恨的别一种形式一样。否则,若待真正到了“山穷水尽”之地步,喜乐固然不存,并连苦愁也一道干干净净没有了,剩下的只有通体的死寂。
在此我特别提出:喜乐苦忧原为一体,统属之于美。喜乐为美,苦忧亦为美。苦、恨、忧、怨、悲、愁、伤、痛,在中国文化从来都是作为美来细细咀嚼的,不了解这一点,就永远不能了解中国文化的深度和广度!
由是才有,那些诗人们,有愁感愁,无愁觅愁,“为赋新诗强说愁”(辛弃疾《采桑子》)。非寻愁也,实寻美耳。
在这个意义上讲,“柔情似水”,那差不多可以称之为情的化身的水,所滚滚流淌的正为一川的美,流到哪里,美到哪里,蓄在哪里,美在哪里;从古至今,吸引了中国传统文化多少的心力,不辞劳苦,千里万里,曲折追踪,去寻她的芳姿,依偎她,拥抱她,远眺近观,抚之摸之,爱之怨之,呼唤之,倾诉之,情不能已,最为知己了。
请看宋人张孝祥《水调歌头•泛湘江》作怎样淋漓的宣泄——
“濯足夜滩争,晞发北风凉。吴山楚泽行遍,只欠到潇湘。买得扁舟归去,此事天公付我,六月下沧浪。蝉蜕尘埃外,蝶梦水云乡。制荷衣,纫兰佩,把琼芳。湘妃起舞一笑,抚瑟奏清商。唤起九歌忠愤,拂拭三闾文字,还与日争光。莫遣儿辈觉,此乐未渠央!”
这是张孝祥任广南路经略安抚使,被谗落职,由桂林北归,泛舟湘江时的作品。全篇散发着一种冰清玉洁的美,不异于一尘不染的仙境。试问此洁此美,是泛舟者自己人格的美吗?是泛舟者所追怀、已然化为一种文化传统的屈原的人格的美吗?都是。而两者于此都一并溶入了那澄澈无比的湘水之中,溶入了那博大广深的造化之中,成为了宇宙人生中一种普遍的美,一种不可拒绝的美,那美与冰清玉洁的神同在!
如果说,这样的美,在西方文化中由康德予以理论总结,被纳入了康德的“道德律令”的公式之中,由西方文化宣言为普遍有效,就同欧几里德几何定律普遍有效一样;那么在中国,并没有这样的思辩律式,而却是从来都以最感性的形式存在着,由那永恒流淌的江水作无言的宣告,宣告“见水思洁”为中国文化普遍的美学原理,普遍有效!
在此,如果说山以其幽静而成为中国文化之半壁栖所的话,那么水则以其清洁成为中国文化栖身之所的另外半边;两个半边合起来共成一个整体,才构成中国文化全部的精神基地,心灵家园。诚元人不忽木《辞朝曲》所言:“则待看山明水秀,不恋你市曹中物穰人稠。”(载《阳春白雪》后集二)山明水秀——对,念念如渴,心之故园,它就是这里,不在别处。
148、归心如水
精神思归的渴念是永恒的。
回归的旅程漫漫长途,是永无止境的。
由是,山山相连,水水贯通,在中华广袤大地上,山与水织成一张密网,任何一处都留下了那思归者的足迹,记载着思归者返归的旅程。
湘水北通长江,被称为万水之母。晋人郭璞激情澎湃地这样赞述——
“咨五才(材)之并用,实水德之灵长。惟岷山之导江,初发源乎滥觞。聿经始于洛、沫,拢万川乎巴、梁。冲巫峡以迅激,跻江津而起涨。极泓量而海运,状滔天以淼茫。总括汉、泗,兼包淮、湘,并吞沅、澧,汲引沮、漳。源二分于崌、崃,流九派乎浔阳。鼓洪涛于赤岸,沦余波乎柴桑。纲络群流,商搉涓浍。表神委于江都,混流宗而东会。注五湖以漫漭,灌三江而漰沛。滈汗六州之域,经营炎景之外。所以作限于华裔,壮天地之崄介。呼吸万里,吐纳灵潮。自然往复,或夕或朝。激逸势以前驱,乃鼓怒而作涛。峨嵋为泉阳之揭,玉垒作东别之标。衡、霍磊落以连镇,巫、庐嵬崖而比峤。协灵通气,濆薄相陶。流风蒸雷,腾虹扬霄。出信阳而长迈,淙大壑与沃焦……”(载《文选》第十二卷)
呼吸万里,吐纳灵潮,天神之大美啊!
这样的心之流,美之滔,精神之巨渊,设若置于西方文化的背景之下,经过一番缜密的逻辑分析之后,出人意料地将被断然排除在美学的范畴之外。请比照一下康德的分析,看他是这样说:“人们立刻可以看出,如果我们称任何自然的对象为崇高,这一般是不正确的表达,尽管我们能够完全正确地把许多自然界对象称做美。……所以广阔的、被风暴激怒的海洋不能称作崇高,它的景象只是可怕的。……它们(按:指自然界里的崇高现象)却更多是在它们的大混乱或极狂野、极不规则的无秩序和荒芜里激起崇高的观念。……关于自然界美我们必须在我们以外去寻找一个根据,关于崇高只须在我们的内部和思想的样式里,这种思想样式把崇高性带进自然的表象里去。”(《判断力批判》)——如果说自然里毕竟有崇高的话,那是“我们的思想样式”带给自然的。
站在康德体系的角度说,这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他是把人的认识分为先天的纯思维与后天的感性材料两部分的,既然人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从后天感性材料中找出譬如因果律、空时律等逻辑范畴,那么这些“思想样式”它必定是存在于人先天的纯思维、即思辩之中,先天思辩将自有的逻辑范畴加诸后天感性材料之上,这才形成我们的认识。譬如“崇高”这样的“思辩样式”就是这样的。
但在中国文化,是从来不这样二分思想的,思想就是思想,混然一个整体,即使最感性的一声叹息也可以蕴含了伟大的思想。中国文化倒宁可认为:是自然将“崇高”带给了我们,将“崇高”灌注我们的心灵,我们因天地神圣而神圣,因山河壮阔而壮阔。
“风急天高猿声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杜甫《登高》)这慷慨激越、磅礴飞扬,是自然与心灵一道的慷慨激越、磅礴飞扬,我心我情即为天心天情,心潮汇同江潮,翻卷高扬,不可自限。
不自限而限,人毕竟难为自然之俦。江潮还在浩荡,而心潮已然衰竭——请继续读《登高》后半首:“……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转瞬之间,滚滚心潮只剩下杯酒勺水。
苏东坡《念奴娇•赤壁怀古》讲了同样的故事,前半阕,面向自然:“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我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激扬飞动,壮怀激烈,人神并为豪迈。后半阕:“……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回首自对时,只有一尊淡酒了。笑,谁笑?笑谁?当然是大江笑我了。
前张而后偃,前豪而后倦,怎么会是这样呢?很简单,还是因为中国文化太过崇仰自然的缘故,面对自然,中国人情甘匍匐自认渺小,承认自然是不朽者,而自己是速朽者。我心弱流细水,只有归入自然之大江大海,才得永恒。——这就是中国文化的“思想样式”。千万不要以为中国文化这样的思想认识是消极的,不,它是完全积极的,正面的,它只是要表明:心灵回归自然、永远积极跟进自然的一种持续不歇之渴念;而非康德那样跳出自然之上,以一“逻辑范畴”一网将自然笼盖于下,思辩称王,自然匍匐。
149、南江美在肌肤,明眸皓齿
李白《峨嵋山月歌》:“峨嵋山月半轮秋,影入平羌江水流。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沁心爽虑,多么空灵啊!
杜甫《南邻》:“锦里先生乌角巾,园收芋栗未全贫。惯看宾客儿童喜,得食阶除鸟雀驯。秋水才深四五尺,野航恰受两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送柴门月色新。”多么田园,多么本真啊!
戴叔伦《兰溪棹歌》:“凉月如眉挂柳湾,越中山色镜中看。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多么澄澈,多么明丽啊!
常建《三日寻李九庄》:“雨歇扬林多渡头,永和三日荡轻舟。故人家在桃花岸,直到门前溪水流。”多么桃源,多么亲心啊!
刘眘虚《阙题》:“道由白云尽,春与青溪长。时有落花至,远随流水香。闲门向山路,深柳读书堂。幽映每白日,清辉照衣裳。”多么幽情,多么恬意啊!
……
“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删稿)波动三千意,水流十万情。实在太多,没有办法随水漂流,巡美这没有尽头的历程了,江南水乡,清、幽、秀、丽、神、逸、韵、雅……那是永远也徜徉不完的。可以认为,中国文化之所以数千年一系,由古贯穿至今,中不改道,一个最其础性的原因就是:这文化早已深深地深入到了产生文化的此一方自然山水的肌里之中,血肉混融为一体,那是再也无法相剥离的了;一脚踩入山水魔阵,流连啊流连,徜徉啊徜徉,再也拔不出脚、脱不出身来了。但我心就愿意这样沉沦自陷。又没学康德,干吗要拔脚脱身?
150、看江看去意,看河看来势
由钱塘、潇湘诸水北溯入江,由长江经淮水北溯入黄河,这时,江南的优美,顿变为北方的浊重,然而却一样的美——或者说更美:美得更内在、更深沉、更有分量了。
江南的美,其美在肌肤,明眸皓齿,风情万种。
北国的美,其美在骨,雄健刚猛,壁立千仞。一如滔滔黄河,天外来河,浊浪排空,千回百转,斩道夺关,奔泻而东。
首先,长江与黄河在观象上就非常的不同。
长江(中游)地处开阔,最宜由上而下,观其去势,一睹那江水远逝、流向天际之胜景,悠长,邈远,在悠长、邈远中浩荡化作舒缓绵延,而人的情感也随江水一道渐伸渐远,一直伸向天地之外,混一于浩茫宇宙之中,不知江流渗入我心之中,抑或我心化入江流、洇入宇宙之中,江、我两忘,天、心合一。
王维诗曰:“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江汉临泛》)
李白诗曰:“山随平野尽,江入大荒流。”(《渡荆门送别》)
又曰:“孤帆远影碧空尽,惟见长江天际流。”(《送孟浩然之广陵》)
又曰:“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
……
心随江水滚滚远去,既浩荡豪迈,又渐行渐远,终而至于转入虚空,转入飘渺,转为一种莫名的怅惘:对江水远逝天外的直观到底引发为对人生终归于不知为虚无还是无限的慨叹。
黄河正好相反,最宜观其来势。
王之涣诗曰:“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凉州词》)
李白诗曰:“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将进酒》)
张蠙诗曰:“白日地中出,黄河天外来。”(《登单于台》)
……
黄河,宛如一条无边的长龙穿行于千山万壑之间,时隐时现,一如来自遥远的天外,降自飘缈的云间,一旦显形于眼前,立即化为一种磅礴的雄奇,雷霆万钧,惊天动地,咆哮万状。而崇山巍巍,广土漫漫,不论这条猛龙如何从天而降凶猛狂野,左冲右突奔肆挣扎,总挣不脱山石与黄土对它的无边包围。从此,这水与土的搏斗便演为一场天与地的较量,或者也可以说是天与地的亲热、亲吻,天与地的恋爱。最终,天地合会,水土亲和,山川结婚,那求动、求变、求解脱束缚的水的无穷蛮力,被本性求静、求稳的山石黄土所收服、内聚,而化作一种绝为深沉的苍凉,将此一方山水中的人们的心灵全然淹没浸透于其中,身心内外获充无限大张力,饱满到要胀破。
黄河之水天上来。来自于虚无,落实为重浊。入海方休。这黄水的历程,难道不正写照了中国文化之下人生那一种不改的宿命?
这便是黄河;便是黄河文化那苍古悲凉的美学特质;便是中国文化倚为核心风骨的特有的、不同于西方文化的那种“崇高”,那种孤拔高岸的美。王维两句诗正为其传神写照:“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使至塞上》)
孤拔却不孤立。长江九派,黄河百脉。在黄河的每一支脉上都无不灌注着黄河的精神,黄河的美学品格——
在黄河的上游,洮河水呜咽着这河水的悲壮:“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前军夜战洮河北,已报生擒吐谷浑。”(王昌龄《从军行其五》)
在黄河的下游,渭河、汾河水摇曳着这河水的沉郁:“秋风吹渭水,落叶满长安。”(贾岛《忆江上吴处士》)“北风吹白云,万里渡河汾。心绪逢摇落,秋声不可闻。”(苏颋《汾上惊秋》)
这悲壮与沉郁是那么的强大无边,不可抵御,以致连“雄图大略”的汉武帝都扛不动,置身其间,所有的欢娱之情立刻全部化为哀婉,留下一阕《秋风辞》至今传响着河汾的声音——
“上行幸河东,祠后土,顾视帝京欣然。中流与群臣饮燕,上欢甚,乃自作《秋风辞》曰: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携佳人兮不能忘。泛楼舡兮济河汾,横中流兮扬素波。箫鼓鸣兮发棹歌,欢乐极兮哀情多。少壮几时兮奈老何!”(载《汉书•武帝纪》)
武帝所悲者,为李白一语道破:“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为青丝暮成雪。”黄河,及其支脉汾水,将所有人都流老了,绝不留有例外!这便是无常,是命运,即使身为帝王,称昊天之子,也不能幸免。
黄河的天外扑来,长江的扑往天外,这一来一往,正界写出中国文化关于人生的周域,可谓其来也无常,其去也无常。位在此两极无常之间的“域”,便是人之为人,其有限现实人生了。那是这样一种人生:其旖旎也犹如江上漪沦,其浊重也犹如河上洪峰。不断的从旖旎滑向浊重,从浊重滑向旖旎,乃至于最后旖旎与浊重混融为一体,分不清何为旖旎何为浊重,旖旎中透着浊重,浊重中透着旖旎,这样一种绝有“滋味”的混沌,也便是中国文化关于人生也罢、关于艺术也罢其总体美学取向,才算作是真的美;除此而外,单纯的欢娱或悲情,只视为小儿嬉戏,不值一哂。
151、英雄善退
如果说滚滚江河象征了中国文化那人生旅程永不驻足停歇的漫漫长途,那么那串串挂在江河主干之上、吐纳江河的湖泽就是此长途旅程中的一个个驿站,给予那些旅途中人以强烈的吸引,吸引他们进到此旅行驿站暂时歇歇脚,喘上一口气。不是说“人生如寄”吗?那么索性,即以寄为寄吧,寄身此“五湖烟霞”之中,暂时也罢总归走出了那令人头昏心悸的永恒流动,以领略一下作为“静”本身的风景,那难得一睹的美。
故此,在中国文化中,入世建功立业虽然光焰烛天辉煌荣耀,而出世退居林泉之下,却得最高的美,更超过于前者。因为,前者不具有人生自足、即自我圆满的意义,它只有人生的展开,却没有人生的收场,只有美学的扬彩,没有美学的收笔。
从消极意义上说,筵席总归是要散掉的,与其没有准备,散后万念俱灰,不如及早抽身,未散之前预先拔脚。从积极意义上讲,进以求功,退以成德,立德立功立言,三立之中德在功前,至德之美乃为至美,与天地齐一。老子曰:“功成名遂身退,天之道。”(《老子》)
老子的教导得到后世无数人持续热烈的响应,数千年间,成为了中华文化绝无异义的最高和最美的追求。
左思《咏史其三》句曰:“吾希段干木……吾慕鲁仲连……功成不受赏,高节卓不群。”
李白《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句曰:“……严光桐庐溪,谢客临海峤。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
最令人惊奇的是,直到清末的1904年,蔡元培等一批志士谋求革命,在上海成立“光复会”,蔡任会长,由蔡元培、陶成章、章炳麟、秋瑾四人共同签署的光复会《誓言》这样写:“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看到了吗?革命是一多么热血精进的事业甚而至于功业,而为此大功业垫底的思想文化及美学意识,却照抄了三千年前老子的原话,一字未改!为什么会是这样?原因只有一条,因为那是一种最高的德行,最高的美,功成而不私占,退开,难道不足可与天地比德、与天地齐一吗?
毛泽东自谓信仰西方人马克思的学说,领导了二十世纪中国最大一场革命,并且获得成功。成功后,毛泽东虽然没有做到功成身退,但在他的意识深处一样有着功成身退的文化的影子,请看他的词《卜算子•咏梅》:“风雨送春归,飞雪迎春到。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俏。俏也不争春,只把春来报。待到山花烂漫时,她在丛中笑。”梅志不在争占春光,只是先期报春而已,待到春光完全降临,百花烂漫,她便功成身退,退隐于万花丛中去了。你可以认为毛泽东氏只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内心里实在并未真那么想。那么我就要问了,纵然如此,毛他又为什么要这样说?明明是显示一种高风亮节之德行之大美嘛。
精进为美,善退为美,为大德大美。
退之为德为美,已然进到中国传统文化之核心观念之中,有一个文化演进的过程。
最初,老庄道家一派提出“退”的文化概念,主旨在“全生保命”,为老庄生命哲学的基础概念之一。到了后来,这概念被儒家接手,而与儒家一个社会伦理的核心观念发生融合,这个核心观念就是:逊让谦退,抑竞止贪。
儒家接手道家的“退”文化观念据为己有,并加入新的含义,这时,“退”之为义,就不特为天道,并为人德。这样一来,道德并举,“退”于是乎广行于社会,而成为一种至善的美德。
至善之德是为至美,上接于天,下接于人,是压倒过其他所有的美德的。林下风致,仙风道骨。还有什么美德能与这种美德相提并论呢?
故曰,英雄善退。英雄不善退只是英雄,大夫钟、韩信是也。善退之英雄近乎神,范蠡、张良是也。
152、老院故宅,精神家园
退,退到哪里去?回答是:一曰退入山中,是为高士;二退退入家中,是为闲士;三退退入“江湖”,鸥鹭为伴,烟霞为友,是为彻底解放之逍遥逸士。就后者而言,越国当年谋臣范蠡,以其人生实践立下的风范为中国文化最高风范。
范蠡智慧过人,帮助越王勾践灭掉吴国后,功成不居,决意退隐,《国语》《史记》均有记载。东汉人赵晔的《吴越春秋》卷十《勾践伐吴外传》这样说:“二十四年九月丁未,范蠡辞于王……乃乘扁舟出三江,入五湖,人莫知其所适。”
范蠡远逝,不可追了,留下一个“五湖”的名儿,成为后世人寄托理想怀抱的胜境和圣地的代名。
五湖实际为哪五湖?其说不一。《周礼•职方氏》注疏等文献以为即指太湖;《水经注•沔水》以为指太湖并其附近四湖:长荡湖,射湖,贵湖,滆湖;《史记•河渠书》索引谓指太湖(具区)、洮湖、彭蠡、青草、洞庭湖。
后世文化对“五湖”确指并没有作认真的计较和考证,“五湖”一词也就成为一种泛称、甚或虚指,举凡幽美水域概泛称为五湖;亦或称为湖江、江湖、湖海、江海,而称呼最多的还是五湖。
李白《书情题蔡舍人雄》:“我纵五湖棹,烟涛恣崩奔。”
杜甫《八哀诗•赠司空王公恩礼》:“永系五湖舟,悲甚田横客。”
任华《寄李白》:“庄周万物外,范蠡五湖间。”
卢纶《观袁修侍郎涨新池》:“微风月明夜,知有五湖心。”
杜牧《行经庐山东林寺》:“他岁若教如范蠡,也应须入五湖烟。”
李群玉《寄张祜》:“越水吴山任兴发,五湖云月挂高情。”
杜荀鹤《早发》:“青云快活一未见,争得安闲钓五湖。”
“五湖”,俨然已与陶渊明的“桃花源”有了相同的含义,成为一个文化理想的胜地和圣地,一个集真善美为一体的自然乐园。真山真水真性情,因真而廉,因廉而善,因善而美。
这美,不特为表面的山光物态、秋水长波之美,尤为在此表面美之态的背后,那传达天命的美之韵,美的精神,以及那万类善自共处,各展其性,俱获天成的自然至善之道。——这难道不正也是善的“心灵”所渴念、所适处的最佳境界吗?难道不是心灵经过多少艰难困苦挣扎努力一定要回归的老院故宅、本真家园吗?
因此毫不奇怪,当误入尘寰、满身伤痕的心灵回马返程,才刚踏入自然故园,便立即得到无上的抚慰:“离别家乡岁月多,近来人事半消磨。惟有门前镜湖水,春风不改旧时波。”(贺知章《回乡偶书其二》)人事是翻覆无常靠不住的,甚至时常是势利无情的,只有那澄澈的镜湖水,波光粼粼,常旧常新,总是张开双臂、以一个母亲所固有的永远亲切美丽的笑脸在等待、迎接游子的归来。
用不着解释,用不着做作,回到故园,当心灵的眼睛才刚与自然之秋波相接的那一刹那,心灵的块垒便立刻全然被融化,而汇入那浩荡柔软的长波之中,随着天运之节奏,一道悠然起舞了:“巴陵一望洞庭秋,日见孤峰水上浮。闻道神仙不可期,心随湖水共悠悠。”(张说《送梁六自洞庭山》)这是怎样一种更超越神仙之上的天乐之美!然而却无可名状,一切俱包含在“悠悠”两字之中,除了悠悠,只是悠悠,无言。
但是,得意而忘言,又何必多言?“水心云影闲相照,林下泉声静自来。”(程颢《游月陂》)那淙淙的林下泉声,岂不就是说尽所有的天言?
此时此刻,即使有愁有恨,也得到内外通透的彻底的涤洗,而成为一种完全没有任何翳蔽、甚至没有重量的、透明的愁和恨,一种纯粹的“轻清者”:“洞庭草青,近中秋、更无一点风色。玉鉴琼田三万顷,著我扁舟一叶。素月分辉,明河共影,表里俱澄澈。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说。应念岭表经年,孤光自照,肝胆皆冰雪。短发萧骚襟袖冷,稳泛沧溟空阔。尽挹西江,细斟北斗,万象为宾客。扣舷独啸,不知今夕何夕!”(张孝祥《念奴娇•过洞庭》)噫!此何言也?只有神圣自然天工,才可将一颗人体血肉之心,重塑再造,而新铸为如此晶莹剔透、清灵明澄之登仙之心,诚王昌龄所谓“一片冰心在玉壶”,李商隐“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苏轼“冰肌玉骨,自清凉无汗”,纯真,纯清,纯洁,纯美;自然,艺术,人境,天境,人心,天心,全然明洁混一,再找不到任何一毫的畛域分界。
153、追求清寒
为此,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精神追随美,其最高境界也就是全力追求一“清”字——像水一样清:“水是眼波横,山是眉峰聚。欲问行人去哪边?眉眼盈盈处。”(王观《卜算子》)追求一“寒”字——像冰一样寒:“长忆西湖。尽日凭栏楼上望,三三两两钓鱼舟。岛屿正清秋。笛声依约芦花里,白鸟成行忽惊起。别来闲整钓鱼竿,思入水云寒。”(潘阆《酒泉子》)
这便是传统中国隐逸文化其最本真之核心精神所在。这种文化相信,“人藏其心,不可测度也。美恶皆在其心,不见其色也。”(《礼记•礼运》)人心为最不透明、最黑箱的所在,最易俗染成污的所在;人心欲善,最首先的是要做到透明,不透明的所谓善心,伪心也。
心怎么样才能达成透明纯善?回答就是,回到自然之中,以自然山水之清纯予以彻底的漂洗,以清纯自然山水内蓄之一腔正气予以彻底的涤荡。
经过自然之神水彻底漂洗涤荡之心灵,它不是“心如死灰”全无色彩了,相反,是喜怒哀乐,五彩斑斓,皆得其宜,皆得其正——
喜则喜天人之共喜:“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风日晴和人意好,夕阳箫鼓几船归。”(徐元杰《湖上》)
悲则悲天人之共悲:“平生太湖上,短棹几经过。如今重到何事,生与水云多。拟把匣中长剑,换取扁舟一叶,归去老渔蓑。银艾非吾事,丘壑已蹉跎。鲙新鲈,斟美酒,起悲歌。太平生长,岂谓今日识干戈!欲泻三江雪浪,净洗边尘千里,不为挽天河(意为不收复山河决不洗兵收战)。回首望霄汉,双泪堕清波。”(南宋无名氏《水调歌头•建炎庚戌题吴江》)
这样的在明净自然中所培育之纯正透明情怀,在洞庭这方浩瀚澄澈之水世界中,经由“宋朝第一人物”范仲淹代笔,陡然升华为一篇仿佛自然本身所发出的最为纯正的“自然宣言”——
“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辉夕阴,气象万千。”“北通巫峡,南极潇湘。”
容汇百川,足够博大。既容得下排空浊浪,悲情无边——
“若夫淫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潜形,商旅不行,樯倾楫摧,薄暮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
复容得下无边风月,浩荡喜乐——
“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耀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宠辱皆忘,把酒临风,其喜洋洋者矣。”
悲喜一时之情,均不失其正:悲则悲天下之悲,而非个人一己之或失;喜则喜天下之喜,而非个人一己之或得。一句话——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便是从古及今贯通中国文化主脉的湖海精神——“中国精神”:心清而淹贯天下,神寒而通摄古今!
154、立地尘世之外,指正尘世之中
湖海精神为天公造化,自然山水所培育,不特是一种情怀,一种责任,并且就是一无可推贷、也无法剥离的权利。
什么权利呢?那就是:自然对人世的权利——绝为纯正的自然有权要求混沌人世去浊返清,归乎纯正。那是清水对浊物的权利要求,天道对人道的权利要求,是一种不可以拒绝的至上要求。
这种要求借乎山林隐士而发出。
是的。这便是中国自然文化其原初之本旨。出世并非为了弃世,恰恰相反,是要在自然之中,背倚高山,脚踏清流,立定一莫可逾越的高度,代自然立言,在根本上为人世供出一个至上的文化参照系来,在此参照系之下,最终为人世之实际运转定出一套规则和准则来,凡合于此参照标尺者为善为美,背离此参照标尺者为恶为丑。——中国文化之自然就是这样立定于世外而鞭策于世中。
《庄子•让王》:“身在江海之上,心居乎魏阙之下。”看为退,实为进,看为无为,实为大有为,看为远世,实为最深入的入世——直探人世之核心,提纲而挈领,执人世之牛耳。
表面上,当人将长长的手臂伸入自然之中,好像要对自然怎么样怎么样的时候,自然同时暗中却把自己长长的触角伸入人世,而捏定人世方舟之舵杆,划定了这小小船儿运行之半径和到达之界域,划定了人能展开其心欲愿望的最大范围。
不错,人常常是自由的,因而常常行为出格,冲出此既定的范围,这时,就要受到来自自然参照系方面的提醒、甚至强有力的纠正和较正,直至人认识到自己错误,诚恳改正,回归到正确的航道——
西湖是美的,美得像一位天女,醉人,使人不能自持。杨万里诗曰:“毕竟西湖六月中,风光不与四时同。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晓出慈净寺送林子方》)苏轼诗曰:“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然而此乃天美,只能敬赏,不可亵渎,只能追随,不可占有。倘若不是如此,不是人境效法天境,却反其道而行之,将天境纳为人境,将清域占作市曹,成为歌儿舞女的温柔乡、销金窟,那么不特其丑无比,要受到无情谴责:“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暖风薰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林升《题临安邸》)亦且为文化和历史所不容:王朝让西湖蒙羞,西湖就让王朝灭亡!
在此,自然美学原则直成为一把悬在天上赏罚人世的宝剑,放射出它那隐含于五湖云烟中直射斗牛的清寒的毫光,让人凛然生畏。
难怪当年孔子曾放言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论语•公冶长》)盖孔子之志,非在以隐求逃世也;而是想换个路子来做做:既然在世中不得行其道,那就转入世外去弘道,也许倒更能奏效。孔子对那些当时的隐士们,从心底里心怀十分的敬意。为什么?因为他们向他显示出了那道德美学清寒逼人的至上的力量,那与西方文化系统中的“自然法”一样在中国文化系统中所具有的同等的理论前提的力量。
155、储纳云水
“自然法”在西方文化和中国文化分别导致的结果是不同的,前者导致法律,后者导致道德。在中国文化,其力量还不仅是为道德理论提供了一个支点性理论前提,而后便袖手旁观无事可做了;它并且作为道德理论的核心组成部分,高高树起一面价值理想的旗帜,向人世日常生活作全面的渗透,而以其无可遏止的力量必使自身得以实现而后已。
清江流韵,非止仅仅潋滟于平野之外,亦且渊默于庭院之中;五湖烟霞,非止空濛于洲渚之上,并就氤氲于堂榭之前。
用围墙围拢起来的所有中国庭院,正成为一个个中国人储纳云水、容蓄自然的家庭基地。他们一代接一代默默地以此为生存基地,自然的方式已成为他们唯一的生活方式。
在文化阶层,则更将庭院予以文化的升级,自觉将小天地中小五湖与院外大天地之大云水连作一片。
《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穷困潦倒,晚年寄居于北京西郊的茅屋之中,他的朋友敦诚曾有诗描述他的居所及生活,这样写:“满径蓬蒿老不华,举家食粥酒常赊。”(《赠曹芹圃》)然而这却毫不影响他的烟霞情怀,他的另一位朋友,敦诚的兄弟敦敏,这样说他:“碧水青山曲径遐,薜萝门巷足烟霞。”(《赠芹圃》,并载朱一玄《红楼梦资料汇编》)
这样的自然烟霞文化理想,一旦与强有力的经济实力相遭遇于皇家或贵族官员手中,便被实现为一种人工山水艺术——中国传统园林艺术。
这种艺术的核心理念只有一个,那就是,将自然山水缩微,浓缩于一个不太大的空间之中,而使人足不出园,即可领略到自然的清雅脉韵,坐在庭堂之上,便可安享高卧世外的幽美雅静。
于是,儒家与道佛,出世与入世,人事与自然,在朝与在野,荣华与清修,立功与立德,外王与内圣,等等一系列传统二元紧张与矛盾,也便第一次在此园林小小一方有限天地之中得到现实的统一,出入进退,随意迁转,再无扞挌。
156、皇家园林上通天
中国的园林源自商周之苑囿园圃。苑囿并称,为蓄养禽兽、供王射猎的园地,或有围墙相围。《吕氏春秋•重己》:“昔先王为苑囿也,足以观望劳形而已矣。”注:“畜禽兽所,大曰苑,小曰囿。”
苑囿又被称为“灵囿”。射猎以娱心,山水以通神,两者并具有宗教至上的含义和功能。故在苑囿中常建有两种中心主体建筑,一为灵台,一为灵沼。
灵台为人工堆制,国王升阶登高之土山。灵沼乃人工凿砌,国王观水观鱼之池沼。登高旨在通天之灵,观水旨在通地之神。兽者,山之精;鱼者,水之精,是自古的成见。由是,国王登山临水,仰观俯察,心领神会,就这样与天地万物神合于一体了。《诗•大雅•灵台》说得明白——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郑笺:“灵者,文王化形,似神之精明,故以名焉。”郑氏复在篇首有注曰:“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祲象、察气之妖祥也。”祲,妖气,云气。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郑笺:“灵囿言灵道行于囿也。”麀,牝鹿。
“王在灵沼,于牣鱼跃。”郑笺:“灵沼言灵道行于沼也。牣,满也。”
不同于苑囿,园圃则为种植菜蔬、花木之所,以篱笆环围。《诗•郑风•将仲子》:“将仲子兮,无逾我园。”《豳风•七月》:“九月筑场圃。”殆即农家之果园菜园。
后世园林,将苑囿与园圃综合为一体,有动物、植物、建筑物,灵台则演化为假山,灵沼演化为池沼,共计五大要素。
不过,苑囿与园圃仍循两条路线发展:前者发展为皇家园林一个系列,后者发展为私家园林一个系列。二者的区别在:
首先,皇家园林保留了通神通天的功能,如汉武帝的太液池,明清北京北海水中之三神山,颐和园万寿山极顶之佛香阁,等等。
在私家园林,其宗教意识淡化、泛化、内化,而演为一种无形的环境美,所谓“神韵”——一种人与自然神意相通的美学境界。只要心灵安适,神与物接,那也就是真正的通天通神了,无须格外再做供奉之事。一句话,信仰已经完全内化、美学化了。中国文化深信,美蕴含了真与善,美中必定有神。美即为神。
其次,皇家园林规模宏大,其建筑物为宫观式等级,有的园子或养有动物(如承德避暑山庄)。私家园林规模小,建筑物为亭阁楼榭廊桥一类,除鸟禽外一般不蓄养动物。
商周时代,苑囿专属于天子与诸侯,有严格的等级规定:“天子之囿百里,诸侯之囿四十里。”(见前引《灵台》郑笺)商末,西伯侯势力崛起,“文王之囿七十里”(《孟子•滕文公下》),属僭制。
秦统一天下,造上林苑,规模宏大,阿房宫即属苑中前殿。秦亡苑废,汉初高祖下令,听民在苑中采樵垦殖。
迨至汉武帝,重建上林,规模更大,围二百里(一说三百里)。其间真山真水,据司马相如《上林赋》的描述:“崇山矗矗”,有九嵕山,南山;水则“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酆、镐潦、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在此真山真水之中,建有离宫七十所,所谓“离宫别馆,弥山跨谷。高廊四注,重坐曲阁。”此外,苑中并建有“颢天之台”,当即周代“灵台”之意。秋冬之季,天子校猎苑中,“历吉日以斋戒,袭朝服,乘法驾,建华旗,鸣玉鸾,游于六艺之囿,驰鹜乎仁义之途。”可见,武帝的上林苑基本仍不出商周苑囿的范畴,还不是后世意义上的园林。粗犷豪放,野性十足,除建筑以外,少有人工精心措置。
据我看,后世意义上的园林,当始于汉武帝的太液池,又称蓬莱池,开凿于元封元年,周回十顷,引渭水入池,池中筑“渐台”(灵台遗意),高二十余丈,并起三山,象东海中瀛洲、蓬莱、方壶三神山。
上林、太液,后世延用其名造苑,东汉有上林苑,故址在今洛阳市东;三国魏有上林苑,在洛阳故城西。南朝宋苑,初名西苑,入梁改称上林,故址在今江苏江宁县鸡笼山东。
汉太液池,在今陕西长安县西。唐太液池,在今长安县北。元明清太液池,即今北京北海及中南海,旧称三海,南北长四里,东西阔二百余步,池上跨长桥,桥北称北海,桥南称中海,中瀛台以南称南海。其间,元时称为华潭,明时又称金海。
留存至今的皇家园林有四处,即北京颐和园、北海公园、中南海、承德避暑山庄;遗址一处,即圆明园遗址。
157、梁园虽好,不是久留之地
私家园林,著名最早的要算西汉梁孝王刘武之梁园,又称东苑,梁苑,兔园,竹园。故址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规模宏大,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
晋葛洪《西京杂记》卷二又记:“梁孝王好营造宫室苑囿之乐。作曜华之宫,筑兔园,园中有百灵山,山有膚寸石,落猿岩,栖龙岫;又有雁池,池间有鹤洲、凫渚。其诸宫观相连,延数十里。奇果异树,瑰禽怪兽毕备。王日与宫人宾客,弋钓其中。”
宾客中有司马相如、枚乘等文学家,后世传为文学佳话,而演为一种文化意识,以为佳士必贮以佳园,一如英雄必配以好马一样,历代讽咏不绝,使梁园一名俨然成为“佳园”之代名,如——
唐张说赞高阳郡王宅邸,诗曰:“梁园山竹凝云汉,仰望高楼在半天。”(《安乐郡主花独行》)
又赞武三思府第,诗曰:“梁王池馆好,晓日凤楼通。”(《侍宴武三思第应制赋得风字》)
李白《淮海对雪赠傅霭》:“兴从剡溪发,思绕梁园飞。”身处郯溪之清,而心羡梁园宴游之盛。
李群玉一反李白意,念及历史沧桑之变,认为不特“梁园虽好,非久留之地”,并且梁园本身亦不能长久。他不羡美梁园,反倒是羡美郯溪,诗曰:“怀哉梁园客,思作郯溪游。”(《腊夜雪霁……奉寄江陵副使杜中丞》)
梁园虽为私家园林,但仍具有王者之气,其“百灵山”正古苑“灵台”之意。由此可以见出,梁王虽为郡国之王,仍然是王,梁园非私家园林之纯粹者。
相比之下,西晋石崇所筑金谷园更具自然之命意,而合于后世贵族园林的标准。园筑于洛阳西北的金谷涧中,涧中有水流过,称金谷水。石崇于《金谷诗集序》中自叙曰:“余以元康七年,从太仆出为征虏将军,有别庐在河南界金谷涧中,有清泉茂树,众果竹柏,药草蔽翳。”(载郦道元《水经注•谷水》)
石崇为当时高官巨富,本身又是名士,故而同类相招,与当时一批贵游兼著名文士结为所谓“二十四友”,常聚会于金谷园中,诗酒唱和,极一时之盛。他们当中,有潘岳、陆机、陆云、欧阳建、左思、刘琨等,均为文学史上著名诗家。《晋书•刘琨传》记曰:“时征虏将军石崇河南金谷涧中有别庐,冠绝时辈,引致宾客,日以赋诗。琨预其间,文咏颇为当时所许。”众诗家唱和之诗结集成书,就是前述所谓《金谷诗集》。
这样,诗人同调,友侪相交,当更合于文士们的口味,不会有“梁园之叹”的感慨。而金谷园既为洛阳的象征,更成为后世文人栖居雅集理想之地的代名,频入诗中——
南梁朝何逊《车中见新林分别甚盛》诗曰:“金谷宾游盛,青门冠盖多。”
唐李益《上洛桥》诗曰:“金谷园中柳,春来似舞腰。”
陈子良《赋得妓》诗曰:“金谷多欢宴,佳丽正芳菲。”
遗憾的是,时逢乱世,佳园到底不是范蠡的五湖,未成避乱之所,反成招摇惹祸之基。二十四友中大部分被杀,死于非命,其中包括石崇本人。佳园中之佳人,丽姝绿珠,一并被祸。佳园也成废墟,引致后世多少人的不尽感叹——
唐刘沧叹:“隋朝古陌铜驼柳,石氏荒原金谷花。”(《晚秋洛阳客舍》)
于武陵叹:“叶落上阳树,草衰金谷园。”(《洛中晴望》)
吴融叹:“繁华自古皆相似,金谷荒园土一堆。”(《题延寿坊东南角古池》)
有鉴于此,唐人彦谦冷了那份历史的心肠,不羡美园,而宝爱于草塘,诗曰:“随梦入池塘,无心在金谷。”(《春草》)
看来,至此中国园林还没有切实找准它的文化位置:园林文化源渊于山林文化、五湖文化,那是一种退的文化,藏的文化,绝不是进的文化,显的文化啊!那是指向自然、指向个人的一种心灵文化,绝不是指向社会、指向市朝的一种政商文化啊!不明白这一点,园子愈是盖得好,园中愈是贮以重宝(其中包括美女),就愈是招摇,原为求适心,反不免于惹祸。
158、何境修得王维来
园林文化之性质,经过多少丧乱,终于在唐代,王维的“辋川别业”中最终得到正确定位。
同金谷园一样,辋川本亦水名,在陕西蓝田县南秦岭山中。唐宋之问最初于此筑“辋川别墅”,别墅后归王维所有,重予修建,山张翠屏,水环舍下,风光奇胜。王维常与契友裴迪泛舟往来其间,参禅论道,吟诗作画,流连山水,不与人事。这真是一件胜事——文化的胜事,艺术的胜事:中国第一山水诗人王维,与秦中第一胜景辋川,不期而遇,引出这样三个大结果:其一是开创了中国第一个诗歌流派,山水诗派。其二是,由王维首创,开创了中国“水墨画”的画法。其三,王维第一个将禅意引入诗歌之中,标志了中国诗歌与中国佛教的第一次正式联姻,这对中国诗歌其审美意境是一绝大开拓,对后来的诗歌史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重塑了中国诗道、诗论的走向;另一方面,也影响了中国的佛教,使这门来自域外的宗教最终完全实现中国化,标志是,由原来的一意苦修越来越走向审美,走向感悟。什么是悟?就是某一天审美天眼的突然打开。苦修变为美修,中国佛教之路越走越畅达,于今仍称繁荣,而印度的原发佛教倒早夭绝继了。——以上所有这一切都可以认为是心灵与自然化合的总结果:心灵化入自然,自然化心灵,于是有了山水诗,有了写意画,有了禅意诗,有了《辋川图》(王维作);“诗中有画,画中有诗。”(苏轼赞王维语),诗中有禅,禅中有诗。从此以后,中国大文化其以审美为主调的性质,就算是确定不改的了。
《鹿寨》:“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清苔上。”——空!但空中有光有人,有物有生命,光、人、物、生命没有一样是硬物,一体柔软流动,觉如空而实不空,一物未灭而就是觉到空——柔空。
《白石滩》:“清浅白石滩,绿蒲向堪把。家住水东西,浣沙明月下。”——洁!同质的多样化,多样化的同质,人、物有起有迄,而一体清浅明洁,看似无而实全有,物物自有而物物自无——洁无。
《辛夷坞》:“木末芙蓉花,山中发红萼。涧户寂无人,纷纷开且落。”——寂!花开花落,无喜无悲。无喜无悲,花开花落。寂非枯,枯非灭,灭非寂。寂中含万有,万有不自有。寂中含万动,万动不自动。——不固执而寂。
《鸟鸣涧》:“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闲!闲如落花,闲如空山,闲如月出,闲如鸟鸣。人闲不自证为闲,闲不外加于人。——非闲而闲。
……
《辋川集》中辋川二十景二十诗,每一首都是这样的宁静,疏淡,意在言外,后人评为“字字入禅”。说眼前景,道胸中事,一景一情,均具象而非象,有限而无限,瞬间永恒,直探造化之本体,达到一种人所能达到的最高的美之境,确可说是中国自然文化的一个奇观了,为后世确立了一个不可超越的文化美学的高度。
159、造景成境,真境在此
超不过王维没有关系,可以效法辋川。中国的造园艺术,其总体的精神建构与美学追求由王维底定,经过宋代的大规模发展,到明代而达到完全成熟,标志就是计成《园治》的成书。
王维的“禅境”那不是一般人所能达到的。王维之后,中国造园艺术是循着营造“意境”这一中心主题而展开的。
意境,更多的是一种诗化的东西,文学化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造园艺术,又是一路朝着文学化的方向来发展的。
造景旨在造境。既然身非王维,无法内感得禅,园艺也非向只有王维式人物开放,则意境不言之妙,就只有借助一种文学化的处理——文学题点——方才得以有效彰显。
文学题额,简直成了唐以后宋元明清中国园林的灵魂之所在,甚至使人疑心,这眼前的一系列复杂安排,山树林水亭阁楼榭,实在倒是为了最终推出那妙绝精警之一额题语而来,就像文章起承转合一大篇铺排是为了完成文章的一句题目似的。
请看《红楼梦》“题园”一回如何触景成文,曲达文心——
“说着,进入石洞来。只见佳木茏葱,奇花闪烁,一带清流,从花木深处曲折泻于石隙之下。再进数步,渐向北边,平坦宽豁,两边飞楼插空,雕甍绣槛,皆隐于山坳树杪之间。俯而视之,则清溪泻雪,石磴穿云,白石为栏,环抱池沿,石桥三港,兽面衔吐。”贾政问题,诸宾客沉吟思想之后,想出“泻玉”二字。贾宝玉不同意,说:“有用‘泻玉’二字,则莫若‘沁芳’二字。岂不新雅?”并吟成一副题联,道是:“绕堤柳借三篙翠,隔岸花分一脉香。”众人称赏不已。
如此一路题下去,“有凤来仪”,“蓼汀花溆”,“蘅芷清芬”,“红香绿玉”……移步换景,一一题出。每题一处额,激活一处景,开出一方境,就仿佛自然之景从人心中流过一样,流入之前,是纯物自然,流入之后,自然化作了心灵,再待从心间流出之后,心灵复化为自然,而此时之自然,已非原初之纯物自然,自在自然,却已成为一种文化的自然,心灵的自然,美学的自然。
自然——心灵——“自然”,这便是中国文化中的自然由原生走向审美的历程。那末一个“自然”,经过人文的题点,已然将人本身溶入其中,而成为一种确切意义上的“天人合一”:自然获得一个灵魂,成为有灵性的自然;灵魂获得一个居所,成为有根据的灵魂。有灵性的自然即非野蛮,有根据的灵魂即非飘泊无依之游魂。
在这一过程中,自然与人,一道成就了自身的“真”性,释现出其“善”性;真善合一,终而达致其最高阶段,进入“美”性。
160、石像开路,留下题咏
中国文化从本性上来说是审美的,既非知性的——逻辑的,也非信仰的——宗教的。知性的真与信仰的善,在中国文化,均不具有独立的品格,而只不过是最终达成美的两个预备阶段。真、善发育为美,真、善在美的成体中释放自己的性状。
所以,在此一种真善美融合为一的文化,终极的解释,是由美予真与善以解释,而不是相反。不是因为真而美,不是因为善而美,是因为美而真而善。中国传统文化就是这样的。
特别予以指出:那个作为中国文化之核心概念的“和”,它根本就是一个美学的概念,不是知性的,也不是信仰的,同时又将知性的真与信仰的善包含其内。和——大美,怎么可能不真、不善呢?中国文化就是这样认为的,毋须论证。
万物相和,是为自然;人与人相和,是为德;人与自然相和,是为道。这便是中国文化的主题大纲,中心主线。美在斯。和和美美。真亦在斯,善亦在斯。
就本章“水文化”而言,江河流韵也罢,湖海寄情也罢,以及园林藏心也罢,说到底,无非讲的一个题目:人与自然的求和。和则美,美则和,在中国文化是一个等价的判断。
相比之下,西方园林所追求和表达的却正与此相反,那是追求和表达一种人竭力跳出自然、主宰自然的文化。
现在仍可看到其遗存:中世纪阿拉伯治下的西班牙,所建哈里发的花园,以水为核心构成,认为若花园没有水,就像天上没星星,后宫没有嫔妃。这一点倒是与中国文化相通:园无水不活,水无柳不韵。但在具体的修筑布置上,就与中国园林大异其趣,其所承袭遵循的仍是古希腊、罗马的美学精神:花园以水为中心,修建笔直的水渠,方正的水池,人工喷水装置……无处不活现着希腊人的几何学理念。横平竖直,却从来是中国园林之大忌。
文艺复兴的意大利,更将西方文化中人乃万物的尺度、自然的主人这一命题推向高峰,佛罗伦萨的贵族园林,无不以建筑为主体,自然居于客位,只成为人工建筑的延伸部分。高大的石柱、雕像,巨型水系装置,壮观的喷泉、瀑布,精心修剪的黄杨树篱,以及由植物修剪而成的各种雕塑造型、图案造型——如“爱情园”即将树篱修剪为一大“心”字,等等,都突出地展示了人在自然中的主体中心地位,展示了人拥有财富、修养、才华以后的那份完全压倒自然的自豪。若是在中国园林,修一个譬如说爱情园的“心”字试试看,情形正好相反,完全一个典型的煞风景!是没文化、没修养的表现,暴发户白丁才这么做。
这种西方式人文精神,在十七世纪的法国达到顶峰,其典型代表便是凡尔塞宫的修建:巨型石柱、雕像,整齐的几何型水池,笔直的水道,雄奇的喷水装置,笔直成行的树木、树墙……所有这一切都以王宫为中心,以透视的角度,按轴线对称的要求,严谨地在王宫前平面铺开,突出表现王宫建筑其宏伟华美之中心主题,及人自由调度自然、安排自然、不可一世的王家气派。
法兰西的美学风范风靡全欧,成为一种欧洲精神。德意志的卡赛尔花园,俄国的莫斯科公园,是为这种精神的异国再版。尤其是前者,其人工建造的数百级阶梯瀑布,壮观之极,巨大的水流,浩浩荡荡沿阶倾泻而下,仿佛天上的天水前来人间赶会,向往此一地上王国,而将这种欧洲精神展示泼洒到淋漓尽致,无以复加,把康德关于雄伟却不狂野的“崇高”的理论落实为现实的艺术景观。
水流向前,道路延伸。以上西式园林,在其每一景观的重要节点上,一般都安置有精心设计的石雕雕像,以为此处景观其中心主题之形象宣示。使一个中国人格外清晰地感到中西文化之间其审方式的内在差异:一般在这些地方,却正是中国园林文学“题额”的地方。
的确,中西文化的差异,其实正可以“题额”与“雕像”、或者说“文学”与“雕塑”的不同予以相区别、相标识:在西方,所崇行的为“雕塑精神”,在中国,则为“匾额精神”。
西方文化哲思,以“实体”承托“物性”的总体逻辑思构为基架,文化的努力表现为通过可感知之外在物性,去不懈追求那隐于物性背后的形而上的“实体”——直至实体的实体——“本体”(上帝)。这种追求是一种“减法”的追求,即层层剥离,去掉那些所谓“非本质”的东西(“偶性”),直至最后剥离尽净,只剩下“本质”自身即“实体”为止,算是找到了最后的“真理”。——显然,这是一种地道的“雕塑”作业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正可确切地称为是一种典型的“雕塑意识”。
相比之下,在中国文化,则以为,决定宇宙流变的物机是一种弥漫不散的“气”,此“气”决不是那种被一些无知的现代人所妄指的什么至微“物质小颗粒”,它是一种与人的心灵相通的“精魂”一类东西,或称为“精气或元气”(倒与莱布尼茨的“单子”有一点点的相似)。这种精气无处不在,却绝无任何形迹。故而也绝没有办法将其作有形的收集展示,更不可能做逻辑的切割、分析解说;只能与神相会,人之神与自然之神通灵,而予以一种美学式的“传神”——在此传神中,人领会感悟宇宙之本真(不是西文的真理)。
那么又怎么样“传神”呢?非易言也。可以说,中国文化所有项目,宗教、哲学、文学、音乐、绘画、舞蹈等等,一直以来都无不在为此努力。显然,面对此弥漫无际、一无形迹之“气”,欲捕捉到它,最佳的办法,不可能是西方文化那种雕塑式减法剥离的办法,而只能是“整体收摄,提炼浓缩”,最后得到一种“提炼物”,便成为宇宙整体的样本;样本像路标似的指示了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