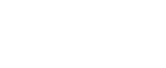山格(十)
178、传统文化的“组织法大纲”
中国数千年道德立国。
在天为道,在人为德,与道相侔,德斯成立。
而人不能升天。
这样,立于天地之间,立地通天的山,便成为贯通天地、接通人神的中介。
古往今来,中国人于是持续不歇地往山上走,去了一拨,再来一拨,浩浩荡荡,长流如江水。
诸山中,最高大雄伟的山,先有不周,继为昆仑,最后是泰山——作为中华群山中的山中王者,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群体“中柱”,也就是“天柱”,担荷起了接通地上凡人与天上诸神的重任,而受到隆重崇拜。主持其事者,为人中之王者。
群体在扩大。地域在扩大。泰山的队伍也跟着扩大,五岳五镇制度形成,东西南北中,分驻中华全境。
于是,群山有了一套秩序:五岳以泰山为首,四岳为辅,五镇副五岳,统领天下群山。
这正对应了人间的一套秩序:帝王——三公——九卿——……下至天下民众。
由是,自然序列“天——山——地”,与人间序列“帝——官——民”适成对应,两相对接,便成为一个从“天”一直下到“民”和从“民”上通到“天”的连续序列——
从前往后,为“递进逻辑”——神从哪里来?从天上:天上的神,传至山,传至地——传之帝,传之官,传之民;
从后往前,为“递归逻辑”——到哪里回到神?到天上:民归于官,官归于帝;帝立于地,升于山,通于天。
而宇宙天地山岳人民,周流回环,圆转为一体。圆转中,秩序生焉。
这便是中国文化的“组织法大纲”。
一纲抛出,长缨无边,宇宙万物就此被牢牢网住,没有谁能逸出。
179、山不变,道亦不变
山,上通于天,通向“神”的总渊源。由此,山本身成为了地上人众信仰的神的渊薮。
山,上通于天,通向“道”的总渊源。因此,山同时成为了地上人众信仰的德的渊薮。
山之有神有德,正犹如银行之有货币。
天与道,神与德,其实是一回事。礼神成德,修德明道,德神道天,并融为一域。
由此,传统文化的山,成为了宗教礼神事务的基地:道教、佛教并扎根于山中。山中修神,将神之光幅射于山外,领导天下众生心灵;
成为了道德修持基地:山中修德达道,将道德的光辉洒向山外,领导世俗精神,校正世俗行为;
成为立学兴教基地:讲经说法,讲道明德,修学立身,内圣外王,以天下为己任,匡世救民,建功立业,既垂范于当世,复留芳于后代,——奖掖人心,敦化人伦,莫此为尊;
成为建根立祖之基地:祖先的陵墓,就立在山中,与山合为一体;如果地平无山,必堆土成冢,以为高陵。《说文》第十四下:“陵,大阜也。”“阜,大陆山无石者。”务必使神圣的祖宗之灵,归于天域。而居高临下,垂训于子孙,永为万世之则;务必使祖宗之英名,建为后代子孙永立不倒的旗帜。
总之一句话,山中文化,为神圣文化;山外文化,为世俗文化。神圣文化为世俗文化的最高参照系,领导、校正着世俗文化。道之所存,标尺所存。
中国传统文化,为静态、稳态文化,百摧不毁,百世不改,其所以静而不躁,稳而不乱,数千年一系贯穿,于今未消者,原因正在于:此文化之舟,抛巨锚于山中,以天柱为碇,从此牢牢泊定,山不变,道亦不变。
180、守护家园
山,不特以其立地通天、永恒不改的精神,贯注人世,成为人世的精神靠山;并以其雄伟高峻、不可逾越的超巨大形体,屏障人世,成为地域生民倚为家园护墙的生存靠山。
长城,根本就是中国自然山势的延伸和完型,作为一道护国大围墙,它只可能产生于西马拉雅以东太平洋以西的中国大陆,因为,这里的山纵横交错,作网格状分割围拢之势。而不可能产生于欧洲,那里的主山阿尔卑斯山,位当西欧约近中央之地,向周域幅射。
于是,中华文明及文化,赖有围墙之山的守护,而以黄河中下游中华腹地为中心,发育,伸展,融合。从上古迄于清代,经过五千年的漫长历史,终于将西马拉雅以东大陆全部融合完毕,形成合地域与文化为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
其间,经过多少战争与离乱,拉锯往复,悲壮苍凉,可歌可泣。而几乎每一次战守,都是以自然山势为棋局,铺陈展开,运智用勇,回肠荡气。
山在家园在,山失家园失。
山水相倚——“山河”,也便成为了中国文化“家园”的最本己象征,引动多少中国人其千古情思。
而“登山临水”,也便成了中国文化一条最根本的“文化理式”,其中凝缩了几乎所有的中国文化的精要:
既凝缩着一个国家的战守之道:居高临下,高屋建瓴;又凝缩着一个人的立身处世之方:自占地步,进退有据。
既凝缩着文化的道德圣义:高标出世,清冽孤拔,俯视群莽;又凝缩着情感的美学要理:登临绝胜,目极八荒,神游古今,融时空为一炉。
既凝缩着国家安邦治国的宏略:居天地之中,四方幅凑,众星拱月;又凝缩着人家长久持家的祖训:高山仰止,身教胜过言教,遗善于子孙,永惠无穷。
于是,在此生命与心灵家园的永不朽坏的高墙的守护之下,田园与人情并进入安谧,安谧中生长繁育,桃红柳绿,粟稷馨香,子孙绵绵,怡然成乐。
中国,就是这样的中国。
181、走不出的循环论
中国就是这样的中国:
在它最胜的时候,它是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群山环绕,大园套小园,园园散发着沁人的芬芳,神仙也醉;
在它最朽坏的时候,它是人间地狱,天为盖,山作墙,密不透风,恶臭熏死鬼。
一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史,记载了中国人的艰难努力,那是一种睡里梦里都在营建乐园,睡里梦里都憎恶恶鬼、与恶鬼作战的历史。
然而,这努力总是陷入循环之中,就像老爷爷在自家的西园作周巡,一会儿在北墙下出阳,一会儿在南墙下入荫。
这几乎成为一种定数:
在太阳底下晒得久了,便生懈怠,昏昏欲睡,一头撞到阴沟之中。大治之世,大乱之基。
进入寒阴,身心凛冽,不能忍受,拼命努力,走出阴影。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除开一元的农业文化其总体机制的基本原因外(见本著第二卷《地格》),就精神状况而言,这是中国历史陷入循环论的道德原因。
但道德之树,生长在山间。罪欤功欤,都在其中。
182、德性比较
就在中国最终将山这边千万平方公里土地最后融合完毕,而进入完全的“天朝”之际,它没想到,一向作为绝域的东边的大海,却透了气,成了域外飞贼袭来的通衢大道:西洋人驾着大型铁甲船,开过来了。
这意味着,传统中国一向自守家园、耕读为德的那份宁静,将被打破。
接着,宁静果然被完全打破:不特中国向来不善其道的海防被打破,即从来善其长的山防,亦溃不成防。
东西南北疆,四面漏气,中国成了一只筛子。
以农耕为基础的、与表里山河相配套的中国的冷兵器,完全不敌以商业为基础的、与大洋相配套的西洋火器。高山绝海,面对坚船利炮,开始失效了。
而在此由高山绝海守护中发育长成的中国文化道德体系,既被洋人宣告为无效——绝无“效率”,亦被中国人自己自省为大而无当不合时宜。
结果,中国人成了懒惰的人:不尚竞争,安居乐业,不是懒惰吗?成了愚昧的人:守土重迁,不谋飞财,不是愚昧吗?成了懦弱的人:不好勇斗狠,不奴役他人,反被他人所奴役,不是懦弱吗?成了散漫的人:自守家园,各自为阵,不是一盘散沙吗?成了无智的人:高尚人情,轻贱物理,没有生产出他们本用不着的新式兵器,去杀人掠地,去强抢贵金属,不是无智吗?没有希望的人:彻底僵化,酣睡不醒,不能自理,死狗扶不上墙,不可救药,完全没有了希望!应该就是由西洋的文明人进来主宰,予以强力开化!
一时间,几乎能想到的所有恶谧,都加给了中国,加给了中国的道德文化,并深入到了中国人的“人性”深处,就仿佛此人性中真的有一条劣根,劣根而劣枝,劣枝而劣叶劣花,周身无不俱劣,连中国小孩比起东洋小孩来,也呆头呆脑成了呆木瓜!
而西洋的殖民主义,口诵圣经,亚非美澳,长臂四达,每到一处,杀那里人民,占那里家园,倒成了他们光荣的证明;全然忘了他们在圣经中,以色列先祖奴于埃及、囚于巴比伦,其上帝之子耶苏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这一段被人奴役、残害的悲参的历史。
为了使殖民主义合理化,一向以唯一追求真理为己任的西方学术也变了调:他们的人类学旨在证出,未发展民族其文化天然愚劣,就该消灭,成了帮助殖民政府出谋划策如何统治殖民地人民的工具。
人们不免要发问:这种文化,其所倡“绝对道德律令”,是说的真话,还是在故作姿态?还是只不过为少数清醒明理人之边缘发言?
西方文化,是这样的好斗:当殖民地抢占完毕以后,再没有开拓的余地的时候,西方列强,他们自己之间打起来了,打一次不解决问题,再打一次,把全世界都扯进来,变成一个鲜血燃烧的世界。
直到二次大战以后,西方自身受到创巨痛深的伤害不说,各殖民地民族纷纷独立,西方世界再也无力予以控制的时候,这个时候,西方的人类学,方才回到“追求真理”的轨道上来,转而论证:文化没有优劣,即使最简单的文化型态,也已然经过了漫长历史的发展,并且对这种文化之下的民族和人民完全合用够用,蛇足反而多余。
这一事实,逼使我们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当西方文化开始公正对待世界其他地域民族文化的时候,那仅仅是因为它到了客观上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并不是文化良心发现。
文化本无“心”。
文化为了协调群体,倡导人为善,纯正人的人格。但文化本身,作为一个意识系统,是“非人格”的,因而也不存在什么悲悯之心。——这一点,我提请人们务必牢牢记住。
人们也许疑惑:怎么倡导所有人均应为善的文化,自身倒会不善?这个问题其实是这样一个问题:任何一个文化系统,都是倡善惩恶的,没有问题,但这样的性质有其施行的一个“边界”,它只施行于本文化系统之下的民族地域共同体,一出这个“边界”,这性质便自动消失,就像地球大气物理性质不存于外层空间一样。
文化,作为一个完整的系统来说,本性上是排斥异文化系统的。
这也就是说,群体倡善于内部,要求群体中的个体成员培养同情心,而群体本身——作为一个“集体”,是非人格的,它在对待其他同类“集体”或个人时,并不具有作为个体人才有的心理属性;它只有客观属性,即较强攻击性倾向或较弱攻击性倾向。
作为许多个体的混杂物——“集体”是冰冷的,同钢铁一样;奇怪的是,却极容易陷入非理性的狂热,实行可怕的攻击:其一,这种攻击是以“集体”的名义发出,因而极貌似打着道德的名义,天然公理,不可追究;其二,许多个体人的“心理”,当其混合为一个整体的时候,既失去了个体独处时所可能有的节制与反省,却保存了个体的“情绪特征”,这种情绪,既盲目,又威力巨大,内涵着风暴一般的破坏性和发泄性。
这便是文化“集体”施暴的原因所在。它比个人犯罪更可怕,发作起来,真的犹如洪水猛兽,冲毁一切,吞没一切。当年法西斯德国残害世界,就都是其实际的例子。
为什么有的文化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倾向,有的文化具的较强的自守倾向,这“禀赋”从何而来?很简单,一切基于“流动”生存生活方式的文化,如游牧文化,商业文化,其生命所在即在于“流动”,因而具有较强的攻击性倾向。攻击什么?即攻击阻滞流动的障碍物,如水之冲毁田土,如风之吹折林木。一切基于“守成”生存生活方式的文化,典型的如农业文化,其内在生命所在,即在于一“守”字,因而具有较强的自守倾向,较弱的攻击性倾向。守什么?守田地庄稼,守生存基地,守望陵园家园。守得愈好,生存愈有保障,否则反是。
因此,商业文化是一种尚动文化,以动为勇为智为德为能。农业文化是一种尚静文化,以静为仁为寿为德为义。
两种文化都崇“变”,但含义却完全不同:商业文化所崇之“变”,更基本的是一种人工之变,由人之智能所造成的变,简单说,是以“人是万物的尺度”的那个尺度算好的变;农业文化所崇之变,则更基本的是一种天然化育之变,一种将人融化入造化之中、随造化节律而动的变。
结果,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位在欧亚大陆的遥远的两端,各自为阵,中国文化守望农田,守望了数千年。西方文化在商业与牧场的混合物中生存发展,贩卖奴隶,追逐贵金属,开拓殖民地,在地中海上空,掀起一波又一波滔天巨浪,刮起一股又一股羊角旋风。三次布诺战争,几乎将地中海搅翻。其结果是造就了一个空前规模的罗马大帝国,直将地中海变作它的内陆湖。从此,西方文化这种以商业为根基的扩张传统,便算是扎定根基,再也不改了。而哥伦布发现新大陆,西方人对美洲的占领,及后来对非洲、澳洲、亚洲的殖民主义入侵,只不过是这种文化的最直接的历史延伸。
这种文化,在其内部,确立了以“流动”为主脉的总体规则,有规则于是而“道德”由以实现——那是这样一种道德:你动我也动,全体遵守规则互动,于是而有了善,有了正义。
但是,当这种文化冲出它的范围,扩张而与其他异文化、尤其是像中国这样的以农业为基础的“自守文化”时——这里通行的是一套“分割守护”的秩序规则,各家守各家的田埂,勿相侵犯,“不争”是为大德——西方那样的如水求流、如风求荡的文化遇到这样的文化时,也便遇到了其天然的障碍物,不是个别的障碍,而是如网一般成体系的障碍,这时,那洪流由于受阻于是而狂暴肆泻,务必将障碍彻底冲毁而后畅。至于在洪波横流的过程中冲毁了多少田园生命,在所不顾——在西方文化本身觉得,这简直就是正义的!相反,那被毁灭的田地,倒成了可怜虫,成了既愚且懦且弱且懒且散、该当受难的被奴役者。不是这样吗?水之与土,水本性要流动,土本性不动,阻遏水的流动,水遇土而成雍,或激或溅,或涌或漫,或渗或淹,而土只是静态地被动承受,这在水看来,岂不是既可恶又可怜,不值得同情吗?
而就在此前不久,十八世纪,西方文化尚未扩张至中国时,两者互不相碍,前者还对后者大加赞赏,称为难以企及的德德楷模呢!眨眼之间,他们便忘了。因为此一时彼一时,彼时他们旨在文化启蒙,正好借中国的道德文化这只手扇他们本国神权政治的耳光,以为新兴的资本主义开道;此时呢,他们的资本主义业已站稳脚跟,到了大规模扩张海外市场的时候,而中国的农耕文化适成其最大的障碍,于是,他们一百八十度转弯,像水仇恨土一样将中国文化视为最丑陋的文化,必欲冲毁而后快。
一句话,近代西方文化水性,中国文化土德,这便是全部问题的症结所在。
183、画法
西方文化水性,中国文化土德。西方文化总是把陆地纳入海洋的国式之中,将前者视为后者的衍生和延伸物,不过是后者的码头或船坞而已。中国文化总是把水域纳入陆地的图版之中,将前者视为后者的组成部分,而为后者提供必要的水源,农业灌溉,做诗。
同一张“水陆图”,这里的确有两种“画法”:一种是画出水域,同时以此为陆地标界——也就是画出陆地;一种是画出陆地,同时以此为水域标界——即画出水域。
两种画法,用的是同一条线,画的是同一张图,一张一模一样的图,但却内含着两种完全不同的文化意识:一种以为“水域”为本体,陆地为附属,是水域围拢着陆地,而给出后者的边界,从而使后者得形;一种是以“陆地”为本体,水域为附属,是陆地围拢着水域,而给出后者的边界,从而使后者得形。
由此,在社会生存领域,也便成为完全不同的两类文化——
西方文化以商业为本体,是市场为工厂标界,交换价值为使用价值标界,货币成了万能的神——为万物标界;
中国文化则完全相反,以农业为本体,农田为市场标界,生产为销售标界,使用价值为交换价值标界,粮食成了万能的神——为万物标界,食即是天。
结果,两种文化代表了两种完全不同的生存生活方式,而有着完全不同的生活信条——中国文化的生存信条是:种好你家自己的地;西方文化的生存信条是,掏出来别人口袋里的钱。
以此为文化中枢,中西文化,从风俗惯制到社会制度、一直到道德类型,都分判于两途,走了不同的道路。
184、道德类型
因此毫不奇怪,西方文化具有着天然的扩张性,早在希腊时代,即十分注重殖民地的开拓与经营。财富外攫,正是海外殖民地的经济支持,才造就了希腊本土的灿烂文明:深邃无比的哲学,不朽的艺术,浏亮的政治民主制,等等。
这是容易理解的:既然生计有了着落,则社会“内部”也就少了生存利益的纠缠,而使得社会公民们,得以像真正的“人”一样,以比较纯清的心态,来关注、讨论比较纯粹关于人自己的“问题”,天才由以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
这样,他们的道德类型,也就成为一种解放个体、张扬个性,这样一种类型,个人越是大放异彩,就越是合乎道德。
相比之下,中国文化的生存环境则完全不同:它立足于内陆,以守护那不能随身携带的土地为最大职事,谨慎守护尚不能作到完全确保无虞,何得弃自己之马,夺他人牛骑,去开拓殖民地?如果说,这种文化有时也竟然去开疆辟土,如汉武帝时代那样,那也是,开辟疆域之后,立即将此疆土化为“本土”,而不是本土之外的“殖民地”。
故此,中国始终只有“本土”,始终被压在守护本土疆域、养活本土人民这样的沉重任务之下,喘不过气来,它的一切事务,都在“内部”,而不是相反。
由本土来养活本土,这决定了,中国人注定将在首先考虑浊重无比的生存问题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再去考虑人性是否可以张扬等一类近乎奢侈的问题。考虑的结果是,不能。因为首先要生存:大家一道张扬,谁去种地生产?
这样也便决定了,中国文化的道德类型,只能是这样一种类型,一种通过抑制人性的张扬而使群体得到最大协调,在协调中保障群体的生存。道德的培养和陶塑,是通过国家的教化,而不是通过群体成员的辩论或讨论;道德教化的基地在静穆的山中,而不是公民的会场。就是这样。
185、道德空间
道德类型其实主要是一个“道德空间”的问题。分析表明,“道德空间”的广狭,与“生存空间”的广狭具有着内在的联系,“生存空间”的广狭制约着“道德空间”的广狭。
其他一切因素除外,西方文化,从其源头处希腊文化开始,近代更得到空前规模的扩展,即历史性地以海外殖民地为本土经济的重要支持,而使本土居民的生存空间得到扩展,大大缓释了其生存压力。正是基于这样的历史背景,西方文化最终形成了他们的以“自由主义”为总纲领的道德体系——这是一种有着较大自由空间的道德类型——
给定一个空间,作为个人活动的私人领地,王国,在此王国内,个人享有绝对自由;只要不出这个范围,就不会影响损害到他人,就是合乎道德的,至于在这个空间内发生了什么,那纯粹是个人的私事,社会无需过问。
西方的伦理学,所一直讨论的,只是要尽可能精确地标出这个空间的地段和边界。研究的目的,当然是如何进一步扩大空间,而不是相反,即是为了进一步解放人,而不是束缚人。
相比之下,在中国,情形正好反一个个儿:其一,以本土经济支撑本土居民的生存,本来就基础性地决定了其生存空间的逼窄;加之——其二,这种土地农业经济,拼命追求粮食作物与人口合为一体的密集生殖,人口密度越来越加大,而更使生存空间日益被挤占,越来越小。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稍微动作大了些,即会影响、扰动别人,这里咳嗽一声,即已惊醒了那里正在睡觉的他人,不能成眠。由此而引致道德空间同步趋狭——你必须老实不要乱动,就是不难理解的了。
狭小归狭小,小也毕竟有个小的空间。更为严重的是,从此文化立定一个展开的方向,那就是,追求狭小,以为愈小愈好,没有最好,而越来越去追求这个小,无穷滚动,终至于,道德空间真的趋近于零数:个人的一切事务,都成为社会的事务,要受到社会的干涉,达到了这样致命的程度:即使你只不过是心里一闪而过、闪了一个念头,也已然潜在地构成了对社会的影响乃至危害,而必须予以清除——除“心中贼”,以防患于未萌。因此便有了,汉朝大臣张敞在家为爱妻画眉,竟遭到皇上的正式过问,这样极端的事例,但在中国文化看来,却是非常正常的,一点儿也不以为有什么极端。
结果,拿出相当的精力去关注别人,也就成了中国人“自己的”、义不容辞的任务,在中国文化看来,那本就是题中应有之义。道理很简单——标定别人的道德空间边界,也就同时标出了自己的边界,否则,不免遭到渗透侵入:邻家女儿的行为可能正成为自家女儿的样板,是不能不关心的!
186、统计学判据
我提出如下判据,供读者参考:
全世界,只有西方国家崇尚“自由主义”的“大空间”道德哲学,也只有西方国家前后一贯地坚持殖主义传统。
西方国家之外,其余绝大多数国家程度不同奉行“小空间”道德哲学,而这些国家都没有前后一贯的殖民主义传统。
我以此一统计学的一致性作为判据,来支持我提出的“道德空间生成论”。
187、西方的悖论
西方的“大空间”道德文化,鼓励个人最大限度去发挥自我,实现自我,作最大胆的奇思异想,最不要命的冒险,摘取金苹果,寻找金羊毛,等等,造就了西方近代工业技术的革命;其海外殖民地,则为其工业提供了最适时、最强有力的支持:资源的,市场的,劳动力的。西方国家由此起家,成了世界强国,世界的主宰。
当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民族主义兴起,殖民地纷纷脱离西方宗主国而独立,这时,西方国家其经济技术体系已然充分发育成熟,到了极为强大、不可动摇的地步,没有“直接殖民地”,单纯依靠其既有的经济技术实力也足以继续主宰世界,于是,他们顺水推舟,放弃“直接殖民地”,而将世界作为他们的“间接殖民地”,以强大的经济技术,无孔不入,渗透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我这样说话,听上去似乎很不好听,他们会反驳说:怎么这样说话!我们只不过是想作生意而已,作堂堂正正的生意,何来罪恶?强壮并不是过错!
而问题是:当由于历史的原因所造就的经济及市场强国,由他们定好条规,让那些同样由于历史的原因造成的经济、市场后进国家与他们“作生意”,这同一个刀客强迫一个农夫与其比武有什么两样?公平吗?反过来,若是农夫强迫刀客比农艺,又会怎样?
可惜锄头不胜刀头,农夫被剥夺了话语权。
结果是预料中的:强国愈来愈得到更多的财富。愈来愈强;弱国不论怎样挣扎,总难翻身。
强国说:这可不能怪我啊!知道吗?我们是公平交易,我可并没有像从前那样,占着你们的领土,你们现在是独立自主的。——他们一字不提,今日这样的现实,原是过去历史的直接延伸。
弱国有话要说,一肚子的话,但说了也没用,只好咬住牙,默默发展自己。
问题在于,就在这个时候,强国倒不依不饶起来,对弱国的“文化”提出质疑,认为,后者之所以落后,是其“小空间”道德文化有毛病,必须予以改造,彻底地改,向西方看齐,现在就改,立即见效。
西方国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一手制造一个悖论:一方面,他们将弱国压住,永远处于弱势地位,不允许跻身他们的好汉俱乐部;另一方面,却又要后者学习他们的文化风度,行为标准,与他们看齐,最好能完全加入他们的话语体系,成为与他们操同一套话语的、因而与他们极好对话的“好伙伴”。
我不知道,这将会造出一种什么样的好结果来!想来,绝造就不出什么“伙伴”,只能造就出“跟班”——小伙计,东家的话,完全听得懂,一点也不“野蛮”,好使得很;要么就是西班牙小说《小赖子》中那位“剔牙”的先生,以富豪们的行为标准为自己的行为标准,强装一派绅士的样子,适成为富豪的“陪衬人”。
“小空间”与“大空间”道德的纯学术比较另说(实际是关于“人性”的一种探讨),就现实的国际交往而言,目前的情况是,弱国欲成为强国,正有待于对自己的“小空间”文化作为借助,以便集中力量,以十当一,而与强国对话,从市场、技术到政治的对话。“小空间”文化倒成了他们可资利用的一种文化资源。否则,资金不足,技术不足,光有人手,“弟兄七八个,围着柱子坐。大家一分散,衣服就扯破。”离开“小空间”,进入大空间,倒是畅快了,却成为一个个散兵游勇,又如何与强手对话?西方国家那么用心用力以消蚀非西方文化国家的文化,欲改造“小空间”为“大空间”,我疑心,他们正有这样的用意。因为,弱国固弱,但将内部力量作大集中之后,一样不可小视,弱小集中力量以抗强、胜强,这方面的例子古今中外多有,不胜枚举。
188、中国的悖论
问题在于,“大空间”毕竟有利于个人的天才成长和发挥,也更合于人性,这却又成为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进行道德抉择时,一个举棋不定的难题,一个悖论。
道德文化或曰价值文化,是文化的总体基座,基座变化,一切跟着变化。
文化其道德空间的大小,直接关涉到文化的内在结构:单一结构的一元论文化,其空间容量总归是小的,譬如说中国传统文化——
天圆地方,一天笼盖一地,一地之上的人合为一家,而在“家长”的率领之下,世代以来,作线形排队,鱼贯雁行,登天柱之山,立地通天,成为这个民族永恒的命定的天职,绝不能作一丝一毫的修改。其文化的空间容量,是早已定好了的,那就是:“天、地、人”这样一个盘面;其内在的行为逻辑,也是早已定好了的,即是:居天地之中,沟合阴阳,接通天地。根本没有余地容纳此秩序以外的任何随意。现在,若作出调整,由小空间调为大空间,必然要触动文化的大结构,就像欧洲的宗教改革那样——
当路德焚毁教皇的诏令,宣布过去的权威公式“人——教会——上帝”为无效,教会无权作人与上帝之间的“居间人”;人有权自己通过对《圣经》的理解和领悟,来决定自己的“良心”问题,而直接神归上帝,公式改为:“人——《圣经》——上帝”,《圣经》成为人通向上帝的惟一中介。西文化的道德空间,遂骤然被放大,人一下子获得空前的解放和自由:我成为我的心灵的裁判者与主宰者,我的裁定只要能交待我自己的良心也就行了,并不需要我之外的他者作为权威进行裁定。以此作为开头,西方社会遂发生根本性的变化,而拉开近代西方大崛起的序幕。
那么在中国,倘若废除天柱山,废去“居间人”,而使人、天直接接通,个人径可以根椐自己对“天意”的理解与领悟,或者,根据自己“某主义”的理解和领悟,来确定自己的生活理想,这样一来,势必引发对整体文化的内在结构、尤其是社会组织法的大调整,其间所必然要产生的社会震荡——在目前全球国际环境如此激烈竞争的情势下——我们不妨自问:中国能否承受得起?欧洲当年宗教改革,所面对的国际环境是,世界普遍处于古代社会的沉睡之中,由是欧洲的改革,正有可以抢先一步的历史机会,不必担心自己在“改革——混乱”的过程中,为外人所乘;待到改革就绪,世界仍然沉睡未醒,欧洲遂淋漓发挥出其由改革所造生的天才与生机,一以当十,洒向全世界,如虎入羊群,把世界牢笼在他们的掌握之中,而财富滚滚如流水,流入欧洲的“世界银行”,欧洲由以在短时间内起飞,由传统社会迈出工业社会,从此,其在世界的霸主地位就算牢牢立定,再无人有能力向其发出挑战。直迄今日,世界依然笼罩在他们那巨大无边的阴影之下,挪动不得,逼使后起的发展中国家,不得不“集中意志和国力”,以十当一,方才勉强在某些方面可以与他们对话。
如此看来,中国现在若欲来一次路德式的改革,改革未可一蹴而就,“集中优势兵力、以十当一”的武器倒先失去,其后果会怎样,就不敢设想了。眼下的活例便是,苏联被肢解,由原来的统一大国,分解为十几个小块块。他们太过于迫切渴望欧洲人那一份“以一当十”的豪迈了,结果一朝放弃“以十当一”的中心凝聚,立即被一分为十。回过头来猛省,再搞什么“联合体”,已是覆水难收,联而不合,为时已晚。尽管由于文化空间被骤然放大,内在的生机遂得以释放,假以时日,必有可期望的良好生长,但这“时日”将会是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殆无疑问。
苏联与中国,向来担任第三世界的龙头老大,作为世界后殖民地国家的领头人,而与作为前殖民地宗主国的西方世界作勉为其难的抗衡。苏联倒下以后,再不成气候。现在西方世界遂对中国予以集中“关注”,他们指望中国亦成为下一个苏联,那样的话,“他们的事”也就好办多了,就像一百年前那么好办一样。而他们长久作“世界贵族”,让全世界作他们的“贵族庄园”,让世界其他国家作他们的小跟班,这样的美好理想,也就铁定不改;谁要想对此世界基本格局作大的改变,至少也是一百五十年以后的事了,到那时,他们又有了更新发展,不愁找不出新的好招,足够对付。
那么中国怎么办?在“大空间”道德文化的“人性当然”与“以十当一”的“现实必须”二者之间,又如何选择取舍?
我曾经说过:自从近代以来中西文化大遭遇,中国的命运就注定是“两头作战”,一头在国际,一头在国内。现在的所谓取舍问题,其实也就成为国际与国内两头的选择问题。设问:重心将放在哪一边?
189、长远与当前
每一个人,即是一个“能量”单元。社会文化,无非是对此所有能量进行疏理排布,安置整合,从而进入一种“装置”,在此“装置”中,原来个体的、因而是盲目的能量,现在进入秩序之中:按预定作有序释放,以免盲目乱爆,炸毁社会。
但是正同机械装置一样,什么样的文化装置,也不可能成为无障碍理想装置,没有摩擦,永不产生代谢废料。怎么样处理装置运转过程中所必定要产生的“垃圾”,是判定一个“装置”其优劣的有效标准。
如何处理“垃圾”呢?到目前为止,“装置”的总体设计,大体说来,无非有这样两类设计:一类是作短周期的即时处理,即时排放,即时清理。一类作长周期处理,即待垃圾废料积累到一定程度时,作一总的清理。前者正对应着“大空间”道德文化,后者对应着“小空间”道德文化——
“大空间”文化,给予个体以较大自由空间,其个体能量,得以随时产生,随时释放,无论是作有益的释放,有害的释放,还是作无益无害的游戏式的释放。总之,不会造成废料堆积,垃圾堵塞;不会造成“能量蓄积,巨大爆发”——这有两种含义:
其一是指,不会造成个体能量的积累坐大;其二是指,不会出现许多个体结为板块,作能量集结。后者的意思是这样的:既然文化“空间”较大,个体在此“大空间”中,得以充分实现“个体化”,个性化程度达到极高,从而弱于从众心理,少有权威人格,千人千性,没有两个人可以雷同重叠,则自然不易产生“同类合并”、能量集结的后果。
与此相反,“小空间”文化则不然:个体未得充分“个体化”,只是整体中之一个“部分”——犹如:不是一个“分子”,而只是一个没有自己的原子核的“离子”,是不“自足”的,因而也是不稳态的,它时时刻刻在寻求进入整体,去依傍一个中心原子核,释放能量,进入稳态。但整体却由于废料垃圾的堵塞,运转不畅,并不能随时将所有这些有待能量释放的游离个体予以吸纳。如此发展下去,离子群集累到一定数量,终于有一天,时机凑巧,大面积的极易结合的“离子”,瞬时集合在“中心”之外的别一中心之下,作能量集结,一点突破,裹挟扩展,迅速铺开,天雷炸响,作能量巨大的大爆裂,颠覆核心,炸翻社会,改朝换代,能量作“大周期”的历史性释放,而对社会进行一次总清算,对“机器”进行一次总清洁,从此开始下一轮的“运转——积累——清洗”的新的循环。——这便是一部中国古代史运动的节律。
中国必须认识到自己社会的特性。中国的改革必须是面向长远的改革——那就是:走出循环。
改革的本质,在于创造一种机制,即使得社会有一套机制,得以随时清理其在运转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料垃圾,尤其是政治垃圾。也就是,在生产工厂内部建立一套配套的“清污系统”,生产与清污,必得是一套贯通一体的自动循环系统。
为此,必须培育社会公众每一个体的“主体意识”,以及由此而生的权利和责任意识。这样,才有真正的“社会监督”,而“社会管理”也就成了全社会的事,而不仅仅是官员的事。
但是,这却又有待于“道德空间”调整扩大。“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这样的旧意识是再不能有了。社会成员必须比较充分地实现“个体化”,即成为真正具有独立性的“主体”;个体只要还有着任何程度的“依附性”,就是没有充分个体化,没有成为主体。非主体,当然无从谈什么权利和责任,那只是一个听取命令和差遣的跟班而已,仅仅是一个符号,一个并不具有任何“本身属性”、只将整体属性作为自己惟一属性的存在而已。毋庸讳言,“小空间”只造就这样的存在,“大空间”文化才造就“主体”。
为了造就一个健全肌体的社会,尽可以开动脑筋对社会政治机构作越来越精致的工艺设计,但一切的基础,仍在道德文化的总体框架的属性。基础不立,不要指望“社会政治工艺学”会制造出什么无缝天衣,创造奇迹。这是肯定的。
“大空间”道德,保护个人有较大个人隐私空间;“小空间”道德反是,保护社会有较大隐私空间。个人愈是没有隐私,社会愈是有大隐私;反之亦然,个人愈是有权保有较大的自己的私人空间,社会愈是少有隐私,愈公开透明。二者成反比,这是一条基本定律,古今中外,没有例外。
190、膨化效应
中国近二十年的改革,是一种“两头兼顾”的改革,这当然是一种最为明智、审慎的选择,即一方面保持传统的“集中”优势,保持以十当一的实力优势,以参与外部交往、竞争;另一方面,同时小心翼翼地对既往“小空间”文化逐步予以调整,由小渐大。
而即使是“逐步”,即使还仅仅只是一种过渡,由于传统上中国文化的道德空间是那样的狭小,几乎压缩成了一个质点,以至过渡还只刚刚开始,“膨化效应”的问题也跟着爆发,并且显示出其可怖的威力。
什么是“膨化效应”?简单说,是指:当一物由原来的小空间、高密度存在状态,由于突然撤去外部的高压力,小空间存在骤然膨胀,膨化为大空间存在,而将玉米变为玉米花,原来形状荡然无存,变得没有面目了。表现在社会生活中,那就是社会犯罪率骤然暴增。
追溯这一历史过程,大约经历了这样一些阶段: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为第一阶段,农村改革,农民复位于“耕者有其田”的传统定位上,立见奇效。
农村改革强烈轰击了城市的心平理平衡,于是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的城市改革——价格改革——中,开始出现一部分人的“经济膨化”,这部分人主要是游离于传统公有制谱系之外的游商,并没有社会定位。然而,经济的膨化,立即引致道德上的膨化,开始冲击传统的“社会等级”,至少在时尚上,这部分人已有欲盖过当时社会的最尊贵阶级——官员——的势头,那时广东流行一句笑话,吓唬某人时就这样说:“让你当干部去!”意谓,让你受穷受苦去。传遍全国。影响所及,“干部”真的有些自惭形秽起来,埋下心理危机。
于是接下来90年代初直迄于今的市场改革中,“干部”们猛醒:噢!我手里捏着可以让人富、让谁富的打开金洞的钥匙,是我让那些人利用“价格双轨制”的空子富了起来,如今我倒反成了没有富起来、被人嘲笑的可怜虫,这怎么可以!于是而一步跨到海边,手握海神波塞冬的搅海大戟搅动起来,把搅起来的鱼鳖虾蟹,无论大小,饕餮吞入肚中,重振“最尊贵者”雄风,痛快淋漓,很快就暴富起来。引动手下胥吏,全面出动,各自为阵,占地为王,但从地界过,留下买路钱,决无通融的余地。连村长也成了可畏的一方诸侯,流行的俏皮话是:“别把村长不当干部!”
道德空间是限定人的自私欲望的容器。换句话说,此容器所限定的,是人的欲望所可以满足、实现的最大边界,一旦超出边界,必伤及公义,影响到别人的正当利益,损伤社会整体秩序。
现在,全社会全面膨化,占地必大,但是哪来那么大空间供所有人都利益均沾?
于是便形成拥挤,空前未有的拥挤。那些先天地利位置占势不佳者,轰然被挤倒在地,被人踩在脚下,呼喊号叫,哀鸣怒骂,但没有人听得见,也没工夫听,在一浪高过一浪的喧嚣市声中,他们的呼喊只如微不足道的草间虫鸣;只有胜利者的旗子在山峰空际,猎猎飘扬。
到处都是爆米花,铺天盖地,一望无边。地在哪里?天在哪里?山在哪里?全退出了视野,剩下的只是一片混沌。大家都埋在由爆米花堆起来的“山”中,攀登这座“山”,成了眼下中国人的最“崇高”之路,通神之路!
是的,这便是现今中国的山。
191、新的希望
膨化效应致使现在中国存在诸多问题,而由此带来的好处却是,使整个社会充满了生机。现今中国人为了求“生”,真是到了拼命的地步。只要当局扎扎实把社会保障事务做好,立定“第一基础”,即安全基础,那么,目前的混乱无序,适证明旧秩序已然开始被打破;则新秩序的重建,是可以预期的。
新秩序,自然是建立在“大空间”道德文化的基座之上,一个既充满活力、又充分稳态的道德文化系统。在这一新的道德文化系统中,原来的“天、地、山、水”四基元,也将获得新内涵:
天:意味着一个新的“理想社会”;
地:意味着一个现代化经济体系;
山:意味着一条新道德之路;
水:意味着一套新美学系统。
而传统文化的基元,也便在新的社会生活和文化中获得新的生命,重现其往日曾经有过的风采,那将是一种立足于东方本土,发枝于中华祖根之上,既造福于中国、也布惠于世界的新中华文化大系。且静心以待。
著者李维加诗曰:
《咏中国山文化》
高拔为欲度攀援?
无限精神无限天。
文章颂起苍岩后,
宝鼎烟升老树间。
一二三生归大道,
百千万战倚长垣。
神州不灭凭神柱,
唤请来人审自看!
(《山格》连载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