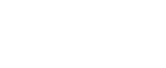无赖肖大
无 赖 肖 大
刘鹤
他走时是个光棍,现在还是光棍,这中间隔着七年,只不过是多了根拐杖。他跛了。
眼前的郁兴屯被一片枯草黄蒿覆盖着,只有那十四座废墟对着兰天,凄凉地证实这曾经是有犬吠有鸡鸣的小屯。可他知道,小屯是为了他才遭此一劫的。小屯的人都逃到哪里去了,他没法知道。
褴褛的衣衫裹着肖大高大身体。他弓着腰,站在空旷沉寂、散发着苦艾味的荒野里,两只细而长的眼睛转动一下好象都很吃力,他像立在蛮荒之地的野人,带着跟猛兽搏斗后的累累伤痕,精疲力竭地又回到了当初的洞穴。命运把他三十二岁的脸孔改成了一副很苍白的面相。
秋风吹开了肖大黑色的衣襟,他用右手遮阳,目光在一座座的小土包上跳着,嘴里说着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的话。慢慢地,对着这片废墟,他跪了下去,开始磕头。
“对不起了,老少爷儿们,我的罪过,我的罪过呀!”他就这样五遍六遍地重复着这句话。一遍比一遍声音大。磕完了头,他原地坐在那里,用衣襟擦着满脸的泪水,然后,双手扣着膝盖,木然地盯着一块长满蒿草的平地。这块平地把他的心揪紧了,他感到呼吸都有些困难。他站起身,索性向那块平地走去。
苦命的肖大,父母早逝,是二叔给带大的。二叔二婶有五个孩子,惟独娇宠着他,认为他太可怜。肖大长到十六、七岁,他要离开叔叔家自己谋生。年龄大些的肖大懂的事也多了。靠叔叔婶婶养活,自然有种张口求食寄人篱下的感觉。再者,他被叔叔婶婶宠出了说一不二怪脾气,就是他叔伯弟弟们也必须事事屈从他。日子一长,弟弟们都躲他,闪他,不愿跟他说话,不愿跟他在一块玩,就是在一个饭桌听饭,也不愿挨着他。他孤单了,这种孤独感让他憋闷。有一次他当着叔叔婶婶的面说出了自己要单立门户的想法。叔叔哭了,然而还是不容许。再后来,肖大悄然离开了叔叔家。有人说肖大出走了。其实并没有走多远,他跑到六十里外的一个小屯,跟一人叫孙四的老头凑在一起。
孙四这年六十一岁,是河北沧洲人。早年当兵时在北京紫禁城当过城门护卫,确实有一身好武功。现在他给大地主周文焕看场院。春夏之际,场院无粮,他也住在场院门口的小屋里。地主周文焕很有心计,给了孙四一支猎枪,不光是让他护场院,一旦他家的四合院有事,比如让胡子包上,孙四还可以在外围接应一下。这样一来,孙四在这小屋里就吃烧足备了。听说孙四练功总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可以倒着爬上院外的一棵杨树。他将胳膊一伸,胳膊上可以吊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而且一点不弯。孙四的轻功又非常好,他纵身一跳,跃上小平房毫不费力。有人说他在少林寺练过武,还有人说,孙中山的保镖是他的师叔。孙四武功被人们传得神乎其神,来拜师的真不少,孙四一个不收。
肖大拜师确有不同。他买了两瓶洒,拎了两条鲤鱼,还带了两包牛舌果子和两包红糖。他将这四样东西放在孙四的炕上,惊得孙四愣怔了好一会。
“我叫肖大,我好命苦,你要可怜我,收下我吧。”说着他向着孙四跪下,磕头,眼泪象泄了闸门的水淌个不停。孙四忙下地扶他,咋扶他也不起,他说:“你不收我为徒,我就不活了。”孙四满口答应了,肖大这才站起。肖大向孙四哭诉了他的身世,还别说,真的打动了孙四。从此,远近都知道孙四收了个徒弟叫肖大,渐渐地,肖大的名字随着师父的名气越传越远。
跟着师傅朝夕相处四年的肖大发现师傅性情很古怪,他不凑热闹。不论屯里来说书的、唱二人转的、耍旱船的,他从不到场,好像他生下来就奔这场院和徒弟来的,其他乐趣根本不懂。
有一年冬天,这屯戏班子脚跟脚来,肖大象过年一样快乐。一天晚上,肖大回到小屋,发现没了师傅,他找遍全屯也没找到。当肖大哭着收拾自己的东西要离开场院小屋时,发现小包里有张纸条:“干好事,做好人,清白一生。”落款:师傅。
师傅为什么走了?到哪里去了?他都不知道。屯中上了年纪的说,孙四手上可能有人命,他怕这些戏班子是在暗访他,便神不知鬼不觉地走了。肖大不相信师傅杀过人,或是在逃难,可他也真说不清师傅究竟什么原因走的。
没了师傅的肖大又孤单了。他没有回到叔叔身边,他要走到一个不知道孙四不知道肖大的地方。这四年肖大除了在师傅那里学了一身武艺,再得到的就是这张纸条了。二十多岁的肖大,这回要独闯天下了。
他带好师傅留给他的这张纸条,漫无目的地走着,他来到了郁兴屯。
郁兴屯不大,总共才十四户,农忙时节十分缺人手。外地的长工、短工聚在这儿实在不少。从未干过庄稼活的肖大凭着一身武功毛燧自荐地上了地主郁占山的炮台。没过半个月,他就被郁占山给轰下了炮台,赶出了四合院,原因是肖大不务正业。那些天肖大只要一下炮台,一准跑出大院和那些穷小子粘在一起。再有,仰仗自己的武功,见了郁占山他也不懂恭敬,用着平起平坐的眼睛对视,用着平起平坐的语气答话。郁占山心里开始厌恶起这个后生。
刚到郁兴屯就栽了个跟头,肖大感到世态炎凉,感到没了父母、没了师傅的孤独,迷惘、凄凉。他觉得这一切既不能重来,也不会复得,命苦,就睁眼去面对苦难人生吧。从此,肖大又跟一个六十六岁的老光棍于瞎子在一起了。于瞎子叫于相龙,他中年死了老伴再未续弦,于相龙并不瞎,只是视力糟得很。一老一少两个光棍结伴到外屯打工,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于瞎子有了肖大这个伴儿,活得有了精神头,每天吃完晚饭,于瞎子总要坐在房前的树墩子上,看着肖大练完功。他虽然看不清肖大的一招一式,只要肖大拳脚带动呼呼的风声,他就叫好。肖大又不孤单了。
三年过去了,肖大和于瞎子这两个光棍顶着的茅草房,名正言顺地成了郁兴屯的老户。
奇怪的是,二十四岁的肖大还没有媒人,尽管于瞎子求了很多好事的,人们都嘴上不停地说着“中”,脚却不停地走开了。于瞎子瞅着这些婉然拒绝的人们,心想还是怨肖大。由于肖大会武功,这屯人怕他,恨他,没有人喜欢他,靠这屯人说媒,肖大非得打八辈子光棍不可。
屯上有个矬子叫温守阳,肖大一见这矬子总要从头上跃过,这温矬子就瞅着地嘿嘿的笑。这天,肖大又是双脚弹起,两腿平伸,像一面墙从温矬子头上飞过。温矬子正侧身同别人聊天,见黑影擦头而过,吓得脸都变了色。当时骂首:“操***,肖大,缺德透了,不怪你无父无母。”
“开个玩笑,何必破口大骂,真是的。”肖大自知理亏退让了一步说。
“有这么玩的吗?无父无母没有家教。”
“再敢这么说,打烂你的嘴。”肖大瞪圆了眼。
肖大从不信神佛,在他心里,父母比神佛还神佛。虽然父母走得早,生活一遭到委屈,他就想起父母,找个角落自言自语一番,其实,他是在向父母诉苦。他总认为父母的英灵每时每刻地伴着他。他不容许别人对他的父母有半点侮辱。
温矬子也恨透了肖大,憋了多长时间怒气总算发出来了。他认为肖大在恐吓他,仰仗身边有三个同心同德的玩伴,他便强硬起来:“说你有父母,哪就把你抬到云彩上去了。”
语言迟钝的肖大再也控制不住心头的火气,脸登时就涨红了,只看他向着一跨,温矬子就四仰八叉地躺在地上了,同温矬子整天混在一块的三个朋友一起扑向肖大,肖大一转身,那三个本不会打架的小伙子,有的捂着脸,有的抱着肚,有的爬在地上“唉哟”不停。肖大指着温矬子他们骂道:“下次有人胆敢骂我父母,我掰下他的胳膊、腿。”说完,他悻悻离去。
肖大会武功,肖大蛮横,肖大欺负人。仅仅十四户的郁兴屯,一个晚上都知道肖大是个无赖。
更让全屯不能容忍的是,肖大赌博输钱从不认帐。为此竟打过邹拐子,李偏脸子,还有小猪倌。到后来,肖大只能是赌场上的看客,没人再跟他赌钱。茕茕孑立的肖大像个幽灵从屯东头荡到西头,谁见了也不同他搭话,像躲着瘟神似的躲着他。
肖大在郁兴屯别说是娶老婆,就是能呆长久,也很是不易。
肖大更不把郁兴屯的人放在眼里,他气着郁兴屯的人,恶着郁兴屯的人。他常说:“郁兴屯的男人不象男人,干活能出老牛的力,遇事就喘绵羊的气,没有一个敢跟郁占山那犊子横的。”
还真让肖大言中了。郁兴屯若有刀光剑影的事,不得不想着肖大。
邹拐子的闺女爱月许给了冯家屯老唐家。马上就到拜堂成亲的时候了,邹拐子家才知道爱月相看唐家的后生是找来冒充的。原来唐家的后生是一只眼。知道了实情的爱月哭了一天,要退回彩礼。唐家人却不依不饶,非要迎娶新人。到了结婚那天,冯家屯来了三十多人,花轿里藏着棍棒,分明是来抢亲。郁兴屯跟邹拐子沾亲带故的也都来到邹家院里,拼着庄稼汉子的全身力气保护爱月。郁兴屯本来人少,就算邹拐子头天各户请一遍,来的壮汉总共十六个人。有人给邹拐子出主意:“快去给肖大磕头,请出他来,一人抵三十人。”
这天肖大还在家睡觉,见邹拐子进屋,将眼睛睁开问了句:“有事?”
邹拐子跪下便朝着仍躺在炕上的肖大磕头:“兄弟,快救救爱月吧,唐家来抢人啦,我们全家求你了!”邹拐子带着哭腔,鸡啄米似的叩着头。
“你看,我病了一宿,现在都坐不起来了。求我等于求泥菩萨,可信不中用了。别耽误事了,快去找别人。”
邹拐子一听好像冷水浇头,一下凉透了心。他从地上爬起来,嘴上说着:“这可咋办呢,这可……。”
看着邹拐子走了,肖大坐起来,眯起两眼,听着街上混乱的吵闹声,心想:这个屯没好人,不用我就背地骂我,用着我,就来当面求我。
邹家院里一场抢亲的混战还是没有避免。邹家亲戚被打伤两人,其他人被打得鼻青脸肿。终因寡不敌众,爱月哭叫得简直没了人声,还是被抬走了。
冯家屯来郁兴屯抢人,这不但是邹家悲哀,也是郁兴屯的耻辱。大家仔细一想,全屯只有大地主郁占山和肖大对此事不闻不问。郁占山是富人,不会管咱穷人的事,大家骂一句也就算了。你肖大混在穷人中为啥隔岸观火,人们不由得把愤恨一下转移到肖大身上,甚至把他赶出屯。
第二天,肖大像没事一样在街上走,往人堆里钻。人们看他来了,先是没了笑声,再是没了话头,接着就三个两个地走开了。肖大心里在骂:“没一个男人。”
事也凑巧,一场大雨又让郁兴屯求肖大了。
前所未有的暴雨足足下了三天,到处是一片汪洋。庄稼都浸在水里。黄岗屯为了保住他们的庄稼,便集合了屯中青壮年要打开拦在跟郁兴屯之间的大坝。这样,郁兴屯就要泊在大水里。郁占山闻讯还是不理不睬,因为他的四合院是立在屯西头的土岗上。有人又想到了肖大。有肖大一个立在大坝,就能阻止黄岗屯人破坝放水。
肖大放出一句话:“要被赶出屯的人会管那闲事吗!”
人们没有去求肖大。黄岗屯的大水还是在郁兴屯走了一趟。郁兴屯的穷人,家家骂着黄岗屯,骂完黄岗屯就骂肖大,骂肖大没人味,吃着郁兴屯的水,旁观着郁兴屯的灾殃。肖大比大地主、大汉奸郁占山还坏,比日本鬼子也坏。
肖大跟郁占山总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的住在一个屯里,然而,万万没有想到郁占山跟肖大还真撞在了一起。在郁兴屯日本人征用的劳工名单上,第一个就是肖大。郁占山是这屯的保长,谁去国兵,谁去奉事,谁去劳工,都是郁占山说了算。
肖大找到大地主郁占山,说:“我有腰疼病,出不了劳工。”
“名单我递上去了,要告病,去找日本人。”郁占山坐在太师椅上,手捋着八字胡,眼睛眯向窗外,不紧不慢不愠不怒地说了这句话。
“洋鬼人是老虎啊,有啥怕,让他们来找我吧”肖大站起来,回敬了这句话。
郁占山将目光从窗外调回,斜视着肖大,语调阴冷地说了句:“那好,我等着这屯出个英雄。”
这句冷雨夹雹的话压得肖大有气难出,他一摔门就跨出了郁家大院。
两天之后,郁占山场院的谷草垛火光将郁兴屯的黑夜照得如同白昼。这天刮着此风,风助火势,火借风威,滚滚浓烟卷向夜空。郁兴屯的穷人没有一人去救火,都站在自家门前看热闹。郁占山望着大火骂了句:“好小子,你吃了豹子胆了,敢跟我斗。”说完他把大家轰回了大院,骑上马就奔县城了。
谁有这么大的胆子,敢跟郁占山作对,郁占山的势力没有不知道的,警察署长见了他还得毕恭毕敬的呢,那还不是因为郁占山的大儿子在给日本人当翻译。全屯的人谁也没敢明说,心里却猜到同一个人。
地主场院失火的第二天傍晚,屯东头的一块空场也点起了一堆大火,这火是用松木柈点燃的。一队日本兵和几个侦缉队的人把全屯老少都赶到了这熊熊燃烧的火堆前。人们正惊恐于日本兵那寒光闪闪的刺刀和狂吠不止的军犬时,就见两个汉奸把肖大五花大绑地押到了火堆前。人们明白了,这里是肖大的刑场。
郁兴屯的人看见肖大还昂头挺胸,满不在乎的样子,大家就更不同情他。大家好像看见一只吃人的猛虎被困在了铁笼里。人们一下想到了冯家屯来抢亲的场面和黄岗破坝淹屯的情景,对肖大能有今天认为是因果报应,尤其是邹拐子,李偏脸子和小猪倌被他打过的这些人,心里暗暗窃喜:“肖大啊肖大,你这个无赖就得日本人收拾你。”人们恨着肖大,恐惧便从脸上消失了。这回轮到郁兴屯的人饱看肖大向大家求救的可怜相了。
就在这时,人群后三个侦缉队的人推着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走向那棵老榆树。人们这才看清,榆树前也有堆没有点燃的木柈。被推到榆树下的老头竟是屯里维持会会长尹万海。尹万海不是为他们管事的吗?人群骚动起来,无数疑惑不解的目光都转向了郁占山和他当翻译的儿子郁文川。
这时,日本小队长征村站在人群前的一块高地,他手拄战刀,用日语向人们讲了一段话。郁文川简单地翻译了一下:“大家不要怕,皇军是来维护你们的安全的。这两个人都不是良民。他俩危害你们的生命,危害小屯的安全。我们不能让坏人再为非作歹。”
郁文川刚刚翻译完征村的话,他的老爹郁占山就接上了。他手指着肖大:“你说,我的谷草垛是不是你放的火?你烧了我的谷草,今天我要烧了你。”
“你那把火失的是天火,是天老爷放的,没法躲过。”肖大毫无惧色。
气得郁占山举着文明棍就奔向了肖大。征村伸手做出制止的动作。他向郁文川说了几句。郁文川说:“皇军要带肖大走,劳工非出不可,怎样处置交给皇军啦。”郁占山拄着文明棍站在那时,恶狠狠地朝着肖大骂道:“让你再多活几天。”说完,他又瞅了瞅那烧得毕毕剥剥的火堆,再看了看肖大,然后,气咻咻地退到征村身后。人们看着那深红的火焰,好象看着郁占山张开的血盆大口,时时等待扑向肖大。
征村提着战刀走近尹万海,唧里哇啦说了半天,郁文川赶紧翻译一遍:“皇军说了,你不是皇军的维持会长,是八路的维持会长,那两个伤员你藏到哪里去了?说出来,马上放你,还要重赏你。”
“我听不懂你在说啥。”尹万海斜了一眼征村。
征村向着围在榆树下的几个侦缉队的人做了个手势,马上一蓬大火又朝天烧起。看着这刺刀、军犬圈起来的两堆大火,每个人的心头,都笼罩着无名的恐慌,好像在参加小屯的葬礼。
有两个汉奸已经把榆树上预先吊着的绳索捆在了尹万海的身上。在场人的心一下都提到了嗓子眼,人们看清了,榆树上的绳索只要一提,郁兴屯穷人的主心骨尹万海就变成了火上的烧烤物了。
就在这时,一个声音像从空中响起,把日本小队长征村也吓得抖了一下。这声音把在场人所有的目光聚在了一蓬大火前,原来是肖大喊出来的。
“别逼老尹头,烧死他他也不知道,八路伤员是我藏的,别冤枉别人了。”他目视着前方,谁也不看,好像对着黑夜说话。
征村、郁文川丢下尹万海,来到肖大跟前。一群日本兵和侦缉队的人也跟着把肖大围了起来。肖大乜斜着征村和郁文川,心想,与其被你们绑着去做劳工,折磨而死,不如就死在我熟悉的郁兴屯。就是死了,我的鬼魂还能回到这小屯,然而,肖大更不想变成火堆上的焦尸,死时还想赚征村的狗命。他想到了东山坞断崖。
“肖大敢承认这种被砍头的事,真英雄。”
“肖大,敢作敢当,有种。”
“老尹头差点变成了冤鬼,人家肖大真没让他顶罪,唉,肖大这小子是个人!”
这些话在有些人心里响着,也在有的人嘴上小声地说着。立时,肖大在人们的心中由过去的魔鬼一下变成了响铮铮的汉子。肖大过去做过那些对不起郁兴屯的事同眼前的义举一比,人们感到从前肖大那样矫情,无非是耍点小性子,是故意的,他毕竟是个大仁大义的人。
场上的目光和火光集中在肖大的脸上。肖大冲着征村小队长又提出了个条件:“我把八路两个伤员交给你们,你们真的放了我吗?”
征村猾黠地咧了咧嘴说:“当然,皇军还要赏给黄金,房子。”肖大满意地将目光从征村脸上移向在场的人们。又看了一眼还在绑着的老尹头,他从容地对征村、郁文川说:“好吧。”
肖大这句话一出口,在场的人都恍然大悟,原来肖大是要用八路伤员来换自己的命。
“肖大怎么可能会不害人。”“他若是不害人他就不是肖大了。”“能拿八路伤员的生命去换富贵,也只有肖大啊!”人们都恨着刚才自己的误会:万万不该把肖大一时当成好人。这号人,真该让鬼子把他烧死。他掉到东山坞断崖多好。人们开始为两个八路伤员担忧起来。
日本鬼子的小队和几个侦缉队的人推着肖大奔东山坞走去。因为山路崎岖不平,征村和郁文川跟在队伍后面。郁兴屯空场上的火光暗下来了。人们知道尹万海的劫难现在转移到了八路的伤员身上了。大家解开尹万海的绳索,看着那队日本兵举着火把向东山坞晃去,每个人的心里都暗暗地骂着这无赖肖大。
刚解下绑绳的尹万海,好半天才缓过一口气。他坐在地上,看了看周围的人,都是郁兴屯的穷人,就着急地说:“快想办法救肖大,是他救了我,救了八路哇!”
李偏脸子站到人群中间,高声喊道:“肖大一个人都不怕他郁占山,都不怕小鬼子,咱这么多人还顶不上个肖大,咱也跟他们拼一把,大不了钻山里。”大家听完李偏脸子的话,都转过身来看老尹头。在郁兴屯的穷人中,大事小情的还要等这老尹头一锤定音。
尹万海仍然坐在地上,低着头,一声不响。大家都不再说话了,空场上只有松木柈燃烧的“扑扑”声。尹万海慢慢抬起头,坚定的目光在人们清冷的脸上扫过。他好像用了全身的力气说出了思考再三的一句话:“郁兴屯,要没了。再等半个时辰,咱也学肖大。”大家互相对视着,明白了尹万海话中的含意。
火把在东山坞的山崖畔晃动着。肖大走在前面,三个侦缉队的人手提着顶着子弹的手抢紧跟在后,日本兵更是刺刀连着刺刀,窜行在山路上。肖大心想,断崖就在眼前了,我要把征村骗到崖畔说话,我要抱着征村跳崖。快到断崖的时候,路也更难走,悬石险石挡道不说,仅容一个人走过的山路也陡起来了。征村、郁文川心上生疑,惟恐肖大逃脱,可左右看了看山洞连着山洞的地形,他们判断八路伤员藏在这儿是可能的,所以他们都胆怯地提着枪吃力地向断崖上爬。
这时,站在山上的一个侦缉队的家伙吃惊地指着郁兴屯喊:“火、火、不好,着火了!”征村用望远镜看了下,递给郁文川,郁文川一看便惊叫起来:“我的家,太君,我的家呀!”在望远镜里,郁家大院已经变成了一个方方正正的红蜡烛。郁文川手抚着大树,野狼似的嚎起来。征村再次用望远镜看过,然而,下达命令,先回郁兴屯。这样后队变前队刚走出五六步,征村命令:停止前进,把肖大押到队前。这时侦缉队和小鬼子才发现肖大正向榛树丛跑去。无数子弹向榛树丛向石堆后边射去,死寂的断崖被一片硝烟笼罩。枪声过后,又恢复了从前的寂静。征村派日本兵在断崖周围搜索一番,仍然没有找到肖大的尸体。他带着满腔怒火杀回了郁兴屯。
日本鬼子举着火把,带着军犬,搜遍了郁兴屯剩下的十三户人家,没有找到一个人。在征村的一通嚎叫之后,那十三座房屋立刻变了十三片火光。
肖大一瘸一拐地在这块平整的空场上转着。不论走在哪,他都要低头想一会,后来,他来到老榆树下,背靠着树干,两眼定定地盯着地上,好像要找出当年两蓬大火留下的木炭。他把目光又移向了那十三块废墟,自言自语道:“哪怕让我见到一个人,让我谢过一个人呢。唉!”
突然,肖大向前拐了两步,转过身对着老榆树,好像找到了在这儿等待他的人,朗声说道:“老少爷儿们,肖大没死,没死啊!”
刘鹤,笔名辰光,亦道,哈尔滨市作协会员。现任哈尔滨市呼兰区计生局宣传站站长。曾在《北方文学》发表小说《寻父》、《天照》等,在省内外报刊发表小说、诗歌、散文、报告文学、随笔76篇[首]
邮编150500 电话139366332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