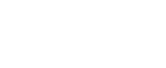水格(五)
98、道法自然,德法自然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家特别钟情于水,以为柔柔水中,大道存焉。
道家极力推广应取法于水,宣言以柔为上的生存之道,于国于民无不为上法:于国家则弭兵息武,干戈不起,于个人则主动退守处下,我不争其谁与我争,百分之百可无确保安全,不受到戗害。以柔为刚,以退为进,以下为上,无为而无不为。一句话,道法自然:水无固形,随物赋形,不固执,不上扬,不恶争,任何曲屈不舒之域,它都可以善为存身,渗透之,充满之,无孔不入,而无声无臭。吁!人性如水,岂不善欤?是为上善若水。
儒家崇山,恒久不改,岿然不动,一如仁义。仁者寿。
儒家崇山亦不轻于水,以为通变流转,不滞不涩,一如智慧。依于仁,运乎智,而安邦定国,天下可得长治久安,永享太平。天圆而地方,智圆而山方,内圆而外方。山是不变的道义,为立国立身之骨架;水是应变之善器,为治世治民之手段。手段上升到本体,荀子以来,触类引伸,总结出足可取法的所谓“水之九德”,董仲舒接手予以推广,遂成一定之论,传说至今。钱钟书曰:此乃“德法自然”(见《管锥篇》)。
道家善水,道法自然。儒家善水,德法自然。道家儒家,乃至整体中国文化,均视女子与水为同类,二者同态、同性、同利、同害。有意味的是,在一般社会生活中,女子同于水,多数情况下是一种美,惹人怜爱;而转入政治历史的范畴,则更强调是一种害,所谓红颜祸水,美貌竟成为了一种不祥,一种可怕。这是可以理解的,在传统社会,女性不具有独立的社会品格,为男性附属,而美女又从来是一种稀有的宝物,对于掌握社会权力的男性来说,一则沽祸,一则丧志,哪一样都不是什么好事。
99、儒释道并祖法自然
中国传统文化,其主要构成习以儒释道三分。三家主张互有同异,历史上曾激烈辩论,互相攻伐。大多数人不加深究,遂以为三家形同水火,黑白相悖;而不知,三家实同生共祖,并出于一源,共以自然为其最高和最终的依据。
在道家,为“道法自然”;
在儒家,为“德法自然”;
在佛家,则“佛法自然”。
只不过,三家会心有异,所取法各有不同。以水为例,道家取其柔,取其广,以为大道;儒家取其变,取其清,以为大德;释家则取其神,取其洁,以为大法。
至于社会习见,民众共识,其取意仍以自然为基础,广泛摄取,混融一体,成为最一般的文化意识,历经稳定性传承,成为传统,如取山譬男,取水喻女,取火譬男,取水喻女,如此等等,纵横交织,最后织就一张有意识无意识的网,散布于民众的日常之中,无时不在,无处不在,而于无形之中指导、规约着每一个人的意识和行为,塑造出一个民族特有的精神面貌。
100、儒家以山为基地,道以水为渊源
中国儒道两家,在一系列学术范畴上成系统两相对立:儒家尚刚,道家尚柔;儒家尚进,道家尚退;儒家有为,道家无为;儒家崇有,道家贵无;儒家隆阳,道家亲阴……这一系列的对立,可以直截了当归结为一项总对立:儒家崇山,道家亲水。
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查其根源,儒家是北方的学术,故以山为基地,道家是南方的学术,故以水为渊源。两家之取法不同,实可从其自然之源头,给以发生学的解释。
101、水中有道
老子曰:“上善若水。”(《老子•八章》,以下只注章次。)怎么样善法呢?他接着说:“水善利万物,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水造利于万物,而自身却身处众人所不喜欢的低洼之地,其品格,实在与“道”是差不多的了。
道是什么呢?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一章》)是无法讲出来的。但却可以观察、体会:道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为天地万物之最终根据;其中,尤其通过水得到最集中、最典型的显性呈现。水的品格正就是道的品格,请看:
其一,道体广大,深广无边,无所不包,一同于水。
老子说:“大道泛兮,其可左右。”(《三十四章》)大道如水,泛滥周遍,无所不在。
又说:“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三十二章》)百川归海,天下归道。
其二,道性无形,充盈于天地之间,抚之无坚,揽之不盈,恍兮忽兮,若有似无,一派柔弱不胜的样子。至柔实为至刚,无所不胜。其以柔为刚、以弱为强的品格,正同于水。
老子说:“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七十八章》)水滴石穿,以至柔克至刚,无坚不催。天下人谁也懂得这个道理,天下人谁也不去实行。
又说:“守柔曰强。”(《五十二章》)“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四十三章》)“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弱,其死也枯槁。故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坚强处下,柔弱处上。”(《七十六章》)柔弱与生相关联,坚强与死相关联。生为真正的强,死为真正的弱。
由水而得柔,由柔而得生,老庄的哲学根本说来,是一种“崇生保生”的生存哲学。于是乎,由此更进一步,一系列的哲学信条以此为出发,被开发出来:
主退抑进:“一曰慈,二曰俭,三曰不敢为天下先。”(《六十七章》)“功成身退,天之道也。”(《九章》)
主静抑躁:“重为轻根,静为躁君。”(《二十六章》)静为动的主宰。
守雌抑雄:“牝常以静胜牡,以静为下。”(《六十七章》)“谷神不死,是为玄牝。玄牝之门,是为天根。”(《六章》)雌静而胜过雄动。
守浊拒清:“混兮其若浊,孰能浊以静之?徐清。”(《十五章》)保持原始之浑厚朴浊,反对人为澄清。
主谦抑盈:“保此道者不欲盈,夫惟不盈,故能蔽而新成。”(《十五章》)永不自满,推陈出新。
主无抑有:“反者道之功,弱者道之用。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四十章》)
主无为抑有为,守拙不争:“我无为,而民自化。”(《五十七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六十六章》)
由天道的本性,推而及于人道,人道由个人的处世信念,归结入于天下的治理,于是而:个人、群体、天地万物,同入化境,清静无为,得至乐而不知为乐,一如广水渊默,永恒为心,人心天心,同归无心。水静川明,续续永生。
102、游鱼入海,相忘于江湖
老子的哲学,到庄子那里,得到了淋漓的发挥,而其中心点,已然由老子对道体道性的静态描述,暗移为人对道的妙悟及取法,取法干吗?曰:取法“水——道”,悦生保命。其强烈的实践性,适成后世宗教文化“修持”之初萌。
其一,道体浩大,同于瀚海,人当弃俗世俗礼,而入此广漠之海,作逍遥之游。《庄子•天地》(以下只注篇目):“夫大壑之为物也,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吾将游焉。”大海泓广,深远无边,百川注之而不溢,尾闾泄之而不干,一如大道,正适合成为心的家,心游于无穷之域,自在之境,无倦无慵,永进永新,无穷无尽。舍此难道还有第二个如此与心的本性适相匹配的场域吗?飞车不可以巡行于蚁道,天马只适合于天行。
可笑芸芸众生,鲜有识得此广域漠海之真面目者,或为井蛙,以井中碟水为世界;或为河伯,以江河线流为天下,最终在海若(海神)面前落得个惘然若失,“见笑于大方之家”:“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尽在己。顺流而东行,至于东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海)若而叹曰:‘吾长见笑于大方之家。’”(《秋水》)
更有可悲者,不知世界小大之辨,以蜗角为天下,争城夺地,伏尸数万。“有国于蜗之左角者曰触氏,有国于蜗之右角曰蛮氏,时相争地而战,伏尸数万,逐北旬有五日而后反。”(《则阳》)拼死鏊战,追奔逐北,十有五日,死伤无算,为的只是争夺一蜗角之地。
小大之辨,关键处在于,要懂得何小何大,如何以小归大,由小化大。人存天地之间,至为渺小,必得归入天地之中,与天地合为一体,方为至大。此时,随天而化,逐波而游,便成逍遥。为要做到这一点,务须做到要能“忘”:忘掉一切的人为,纯依乎天然,依乎道,就像游鱼入于大海之中,既忘却鱼外之鱼,忘掉身外之水,并忘掉身之为鱼,这时,鱼与水,鱼与道,鱼与鱼本身,方始浑然归一,而得性命之正。“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呴以湿,相濡以沫。与其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鱼相忘于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大宗师》)失水之鱼,方相呴濡;失道之人,方相亲爱。反之,得水得道,而亲仇爱恨,也便一并消解,进入大化。
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在鱼,必须先识得细流广水之分;在人,要识得小得大道之辨。怎么样才能获此高识?其实也很简单,不必去刻意追求什么,要把一切的“有心”全部消弭,变有心为无心,无心之中,便天然归道了。正犹如:“鲵桓之潘为渊,止水之潘为渊,流水之潘为渊”(《应帝王》)心如水体:水体无心,动止随天,或鲸鲵盘桓,或螭龙腾跃,或凝波,或湍流,情境种种不一,而水体渊默无心,自在随化。
山不动,水动。水有时动,有时不动。不动亦道,动动亦道。人如山如水,无不可随化入道。要在能做到像水那样,动亦出自无心,不动亦出自无心。
103、人心如水,性命如水
人心如水,守其本性,便一切俱得,动静皆宜:“其动如水,其静如镜,其应如响。”(《庄子•天下》)动如流水,静若镜照,应击而响,神应敏速,略无迟滞,自入大化。
这其中,“其静如镜”是最为关键的基础。只有静下来,才能心明如镜,应景而照,烛照万物,而认识真理,获悟大道。其情景,绝类于水——水静而明:“圣人之静也,非曰静也善,故静也;万物无足以铙心者,故静也。水静则明烛须眉,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圣人之心静乎!天地之鉴也,万物之镜也。”(《天道》)一旦心静如水,则精神如神之光(借用西方文化的说法),足以穿透万物,万有均入精神之巨镜之中,纤毫毕照,无复再有遮蔽,而心灵得见至道,进入真境,进入永恒自在之域矣。
但是,这所谓“静”却绝不是佛家的“寂”,即不是死静死寂,不是寂灭,不是除灭所有心念,转成为空。这一点是至关重要的,通常总为人所忽略。这里的“静”,即老庄道家的那个“静”,是指:一种全然去除“人为”而纯任乎天然,在这样的意义上的“静”;只要你彻底去除了“有心”、“刻意”、“有意”等人为,而一颗天然之心作天然之或动或静,哪怕静如死水、动如雷电,就都是“静”,静也是“静”,动也是“静”,一切动止无不“静”。这就是所谓“自然”,就是“无为”。这是老庄哲学的中心要领。得此要领,便领会了老庄真谛,同时也了解了道家与佛家的根本区别。
《庄子•刻意》说:“水之性,不杂而清,莫动则平。郁闭而不流,亦不能清。——天德之象也。”
这是很关键的一段话,意为,水的本性,只要不杂外物,就必然清澄;只要不外力扰动,就必然平准;水既清且平,天镜皎明,就必然鉴照万物不遗,纤毫无隐。死水郁闭不流,必成腐液,如何能清?必当是活水——即流动之水——方才得清。此之为“天德之象”,为天道之显相(在更严格的意义上讲是象征)。
看,这不是讲得很明白吗?自然之水,永恒周流,当然是流动不闭的。那么,就取此法,任其自然逍遥周流就好。人心亦如是。只是不要杂以外物,不要杂以“人为”,一旦“人为”,必杂外物,即非纯乎自然,即不能“清”,不能鉴照了。
然则,像佛教那样,人为刻苦,一意要将心中的所有心心念念(不只是杂念,而是所有的心念)全部铲灭,就恰恰是“人为”,而且是最大的人为,就非自然了。
此外,如儒家的仁义礼智那一套,也统统是人为,有违于天道,“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知北游》)从道一直滑向礼,形成一种无可挽回的沦落,其罪由只是出于“人为”。这便是“乱”,乱什么呢?乱心而已矣。
礼之核心在忠孝,而忠孝,戗害性灵,实祸莫大焉:“世之所谓忠孝,莫若王子比干、伍子胥。子胥沉江,比干剖心。此二子者,世所谓忠臣也,然卒为天下笑。……皆不足贵也。”“比干剖心,子胥抉眼,忠之祸也。”(《盗跖》)
至于普通人,身无比干、子胥之贵,没有机会因欲强作忠臣而遭剖心沉江之祸,却也不免于在他们那个小民细行的层次上犯与比干、子胥同样的错误,那就是,向虚背实,追声逐影,人为加鞭,力绝而死:“人有畏影恶迹而去之走者,举足愈数而迹愈多,走愈疾而影不离身。自以为尚迟,疾走不休,绝力而死。不知处阴以休影,处静以息迹,愚亦甚矣!”(《渔父》)崇阳而恶阴,崇有为而恶无为,直至绝力而死!扪心自问,世上又有几人不是这样的呢?真是可悲可怜啊!
怎么样才能走出此可怜的命运呢?简单得很,取法于水,纯任乎天然:任其清,任其淡,任其平,任其无心,一言以蔽之,任其无为而已矣。
“庄周曰:吾守形而忘身,观于浊水而迷于清渊。”(《山木》)
“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充符》)
“君子之交淡如水,小人之交甘如醴。君子淡以亲,小人甘以绝。”(《山木》)
“鱼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术。”(《大宗师》)
能做到以上这样,方始最终获得解脱,而得天乐。“知天乐者,其生也天行,其死也物化。静而与阴同德,动而与阳同波。”“其动也天,其静也地。”(《天道》)没身于天地阴阳之中,与天地同行,与阴阳俱化,就像鱼入大海那样,而将天地至贵之生命安置于完全适合于其本性之广川巨渊之中,对于拥有此生命、最有责任全力呵护此生命的那个你和我来说,难道不是最善最应该做的选择?
104、清静为治,不撄人心
这一点,对于统治者人王来说,尤为重要,因为:他们是万人之主宰,不特主宰着自身的生命及其祸福,亦且主宰着所有人的生命及其祸福。为了所有的人,为了自己,作为王者,他格外需要水中明道,以水为法,率领天下人一道进入无为。
“何为道?有天道,有人道:无为而尊者,天道也;有为而累者,人道也。”(《在宥》)
“古之畜天下者,无欲而天下足,无为而万物化,渊静而百姓定。”(《天地》)
“一心定而王天下。……一心定而服万物。”(《天道》)
王者诚能做到如深海一般渊静澄清,天下万民之福也。
王者切忌抱薪救火,妄自扰动人心。人心如水,任其天然,则动静成趣;一旦人为搅动,掀起巨澜,洪波涌动,就危险了。这时候你会看到,一向脉脉柔柔的水就会显示出它的另一面,那席卷一切、披靡一切的极为可怕的一面。那时,待人心乱了你去救世,洪水来了你去治水,可就如大禹治水一样,格外的艰难了。“人心险于山川。”(《列御寇》)这应该成为一句铭言,刻在所有经世者的心间,须臾不可或忘。
说人心奇险,这不是荀子的性恶论——认为人性生而为恶;而是说,人心生而渊静,人不应该人为扰动它以致乱心。以天道化民,无非是使人回复到人本来就有的天性而已。相反,不去化,而去扰,只有自食恶果。
“崔瞿问于老耼曰:‘不治天下,安藏人心?’老耼曰:‘女(汝)慎无撄(扰)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绰)约柔乎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凝冰。其疾,俯仰之间而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天下。偾骄而不可系者,其惟人心乎!’”(《在宥》)人心居静,渊渊默默。一旦扰动,排他居下,进己在上,诡上诡下,柔弱制服刚强;雕琢名行,顺心则生喜,如火益热,违情起怒,如冰益寒;变化神速,一念之间,驰赴无极之地;安居本静,触境而动,成高天之悬。偾发骄矜,不可禁制者,其在人心乎!
这样含雷蓄电躁动不朴之人心,如果千百万汇聚,翻卷成滔,东奔西突,上摩下荡,裹挟撕扯,喜怒不测,变化万端,从人类诞生以来就成为人类如何组织自身的一个不解难题,巽化还巽化不过来呢,又如何敢大胆去扰动它呢?
文化也者,也正就是为了索解此难题而生。为了组织、协和、调适一堆乱哄哄的人群,文化将失巢乱蚁一般人群汇集一体,组织为有序的、可以协调运转的社会群体。
为了这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社会群体的安静保持,我们看到,老庄开出来的方子是:去人为,任天然,水德清静,回到纯朴。后来的实际历史,虽然未可依此全方设计国家,安邦定国,但也极为深刻地深受其影响,中国古代历史尽管治乱交错,大起大落分合不定,而崇尚纯朴,则始终一贯地作为社会文化的最高理想、最高价值之一,众口一词,历代无异。这样的文化理想,并深入地参与到实际的历史之中,而强韧不歇地校正着历史实际过程中过分的“人为骄矜”,虽然并不能时时处处起到立竿见影的神效,却为历史的长河画定了一条无形的流向,而使得此历史之河前后保持一贯,总是朝定一定的方向,在一大体不变的流域中向前流动,没有发生根本性的改向。至于实际历史的具体操作,则更多地取术于儒家文化,下一节中我们将会看到儒家所倡“水德”文化在传统中国历史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实际发挥的重要作用。
105、运智如水
道家、儒家均以关怀实际人生为其学术鹄的,而主旨取向不同:道家主旨取向在个体,欲使社会群体中每一个体适性而生,更少受到来自群体之蛮横束缚,故倡“无为”。无为也者,道家首先是对政府统治者说的,要他们对他们所统治的百姓多无为,少干涉;其次说与个人,要他们对待他人时多无为,少干涉。这是道家学说的实质用心所在,说白了就是这样。众水分流,各奔自己的流向,毋得互相干涉,像前面曾说过的黄河决口、改道夺淮那样,就不特黄河失性,连淮河也给害死了。
与此形成对照,儒家学说的主旨取向则在群体,力倡有为,欲使世道归善,社会有序。为此,社会中每一个体必须适应群体而不是相反,要按规矩来,要受群体的约束,要自我约束;个体自我约束不到,群体有责任帮助其怎样养成接受约束的好习惯。蓬生麻中,不直也得直。众水分流是分流,但必要时也要合流,互相取长补短,互相监督。黄河浊,淮河清,那么就来个“借淮刷沙”,以此防止泥沙淤塞。为此儒家与道家相反,不是主张取消干涉,而是要积极干涉。君德如风,民德如草,风行草偃,一定要以上化下;风不拂草,上不化下,反而倒是失职,没尽到责任。只不过,这种干涉应是一种良好的干涉,而不是恶劣的扰民,是借淮刷黄,而不是借黄淤淮。说白了,儒家想要的是:好政府,好干涉,最后达致全体一致的好民众,政府率民众一道进入大同理想社会。
这样一来,“水”的文化含义及义理位次,在儒道二家的理论系统中便大有不同。如果说,“水”在道家理论中处于最高的“道”的位次,水即天道,或天道之象征;在儒家,则处于第二的位次:第一是仁,第二才是智。山为仁,水为智。
孔子曰:“知者乐水,仁者乐山。知者动,仁者静。知者乐,仁者寿。”(《论语•雍也》)康有为《论语注》综合前人的理解,注曰:“知者达于物理,而周流无滞,故乐水。仁者安于义理天命,而安固好生,故乐山。知者才智迸发,如机轴转运,不能自已,故动。仁者神明元定,如明镜澄澈,粹然无欲,故静。动而周流自得,故乐。静而安固有常,故寿。”
很明显,这时,仁与智,山与水,前后双分,处于不同的位次:前者为义理,后者为器用;前者本体,后者花叶;前者为根据,后者为事功。义理崇常,天道永恒,故得之而安,一如高山,千秋耸立,巍然不动。孔子当年赞扬尧舜之德,就是以山为比。是为仁。是以不变足以应万变的东西。器用则求达成事功,故尚变,一如流水,周行不滞。但变来变去,其出发点和归宿都不是“变”本身,而是指向那个不变之本体,指向仁。为什么要运智成事?目的只是仁。从仁出发,最后仍归结为仁。是以万变而最后成就那个不变的东西。
仁居第一位次,智居第二位次。仁为一,智为多。仁为简,智为繁。一句话,仁义为“内圣”,智用为“外王”。
由此,道儒二家之取法于水,含义也就十分的不同:道家取法于水,称谓虽多,取其深广,取其渊静,取其柔弱,取其清明,都是一回事:取其道而已矣。在儒家那里,继孔子总论排定山水位次以后,后儒进一步多方开掘,发明出多重文化含义,而总归仍不出智用的范畴。
道家,道法自然。儒家,德法自然。
106、德治九法,无为为首
儒家始祖孔子、孟子着力于建立他们的基础理论,仁义礼智云云,至于这理论的实际运用,具体究竟怎样去落实,怎样去建国立国治国持国等等,就讲得比较少。这种情况,至先秦最后一个综合性大儒荀子那里,为之一变。荀子非常仔细地考察了实际经营一个国家所可能用到的各种“手段”,什么“王制”、“王霸”、“君道”、“臣道”、“富国”、“强国”等等,都做过认真的分析论述。其中,荀子对如何运智如“水”,做了全面的总结。
荀子德法自然,总结水有所谓“九德”,他是这样说的:“孔子观于东流之水。子贡问于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见大水必观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徧于诸生而无为也,似德。其流也卑下,裾拘(水流曲折)必循其理,似义。其洸洸乎(水流汹涌)不淈尽(枯竭),似道。若有决行之(决水使流),其应佚(快速)若声响,其赴百仞之谷不惧,似勇。主量(以水衡平)必平,似法。盈不求概(概:量米刮平用器),似正。淖约(绰约:柔弱)微达(无所不到),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鲜挈(洁),似善化。其万折必也东,似志。是故君子见大水必观焉。’”(《荀子•宥坐》)
以上水之九德计为:德、义、道、勇、法、正、察、善化、志,属入世所以治世之法。其中第一条,“无为”之德,似道家言,其实不然。儒家亦讲“无为”,而不同于道家“无为”义,它不是道家那种意指个人率动归命、返性达真的生命立场,而是儒家为“立国治国”提出的一种重要思想,其义盖有如下三端:
一则为,立国尚简不尚奢,保民养民,教民化民,不可扰民害民。在这个意义上讲,在实际防民治民的行政统治过程中,要尽可能做到清简无事,少给百姓找事。后来历代王朝,虽然事实上扰民之事并不少见,而其立治从简的统治总方略,却并没有变。尤其在中国的乡村,从来着重于宗族自治(孝文化的结果),尽可能少与官府打交道,官府也尽可能少地插手乡间由宗法可以处理的具体事宜,乡民与皇上——两逍遥,不能不说是这种施治方略长期实行所养成的结果。
其二则为,政体的实际运行,儒家历来主张,士人为文化道义的承担者,监护者,他们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天然使命和责任。以故,士人的首要核心任务便是:上则为帝王之师,教导、监护帝王,使之一切言动归于道义,做有道之君;下则牧民教民,使百姓有养有德,安居乐业,做王化之下合格的好子民。这两项工作做好了,国家达致大治,君圣民贤,是为太平盛世。这就叫作:君无为,臣有为,君虚臣实,君逸臣劳。(这个思想集中出自《吕氏春秋》,容后详述。)
其三,在士君子不懈的教导和监护之下,君主圣德如天。其时,君德如风,民德如草,以君化民,风行草偃,全国达致大治。此为“德治”之最高境界。这时君主不必再劳心费神施行什么治民的措施,只自己做出一个良好的榜样,百姓自然而然跟着走,就一切都好了。这是一种最好的“治”,不治之治,无为而治,不治自化,也叫作“垂衣而治”,是儒家文化的最高理想。这种理想不是空想,儒家指认说,当年尧舜时代就曾真的实现过。
关于尧舜故实,今日的我们当然明白,那不过是儒家者流的一种“理论设定”(借用传说)。但可不要小看了这种设定,它是儒家全部理论的总目标和总归结,它的全部理论赖有此总目标而得支撑成立。(正如共产主义社会之于马克思之整体理论体系那样。)而中国实际的历史,也决定性地受此理论的影响,确定了其历史的总走向,确定了中国历史的总格局。中国传统社会,一以贯之追求道德治国,在君,要求内圣外王,集圣者与治者为一身;在臣,要求德学兼备,集为师与为官于一身;在民,要求淳朴忠良,自我约束,集劳力与服从为一身。——以上君士民三项理想范式,归根到底,无非是此“无为治国”思想的最后的总结果。
“无为”,意味着“有德”。此德即“水德”,乃荀子水之九德之第一德!
水德第一德立定一总纲,辅以其余八德为目,义、道、勇、法、正、察、化、志,而儒家一张经邦治世之文化巨网,遂由以织成。一网撒出,中国历史遂由以被罩定。这时,儒家学术转身而成为一套治术,儒学之学成为官学,也就是当然的事了。
由此可见,“仁者爱人”,儒学义理如山,安固于后;智者治世,儒学治术如水,圆转运筹于前,就应时成变,涉变成理,涉变成事,涉变成趣,涉变成诗,千变万化,周遍适应,儒治确乎将统治与诗意一炉融化,在世界经国史上,也成一绝。
107、义、勇、道、法、正
义。义者宜也,应该之谓。仁以安人,义以接事。行事必合于义,方立身治国,使道德有所落实。义在孔孟之教中处重要地位,孔子曰:“义以为质。”(《论语•卫灵公》)朱熹注:“义者,制事之本,故以为质干。”至孟子,更明确列“义”入仁义礼智四端中之第二位,并定义为明辨事非。汉代,董仲舒再加一“信”,而合成三纲五常之五常,以后遂成为中国文化系统中治国治民之纲领性信条。
道。董仲舒曰:“道之大原源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此道非道家“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那个道——那个道是天地万物之总根源,其中天亦为道下之属;此道为人世之道,具体讲,为人世间人与人之间关系之道,那就是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纲,仁、义、礼、智、信。
勇。孔子曰:“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论语•子罕》)心怀正义,义胆通天,必无所畏惧。“仁者必有勇。”(《论语•宪问》)诚如水之决行,不屈不挠,义无反顾。
法。原始儒学罕言法,战国末开始学术融合(荀子为最重要的代表),汉以后适应实际治国之需要,官学儒学更将既往百家学说予以综合吸收,其中由法家主倡之法的思想,遂融入儒学之中,成为其重要的内在组成部分之一。就文化而言,法的意义,本质为公平。统治者接受它,是由于它为统治者的统治提供了其所需要的简单易行的行政工具;大众接受它,是它为广大民众提供了一种他们实际想要的现实。于是而,以自然为法,执法如水之平,不偏不倚,遂不仅上合于天理,并下合于人心,而成为中国文化特别根深蒂固的一种意识。俗语“一碗水端平”、“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千年轰传,众口一词,就是这种意识的具体表现。
正。守身持正,不越本分。正犹如水,满则自止,不待帝命,所谓“盈不求概”。用西哲之术语说,当即为所谓“自律”。概者,古时量米时用以刮平斗斛的器具。为人为政,也要如此。身教胜于言教。孔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论语•子路》)
108、察:水镜、心镜、人镜
察。如水无所不照,在人洞烛幽微,无物或隐。《史记•五帝纪》:“聪以知远,明以察微。”明察,实为智的最首要前提。既明于察物察人,尤严于自察自明。察物以知物,察人以知人,自察以知己。心如明镜,内外通照,洞达于世。这便是中国文化特出的“借鉴”的思想。
鉴者镜也,最古老最大一面镜子,它就是水。取法于水,以水为镜,而万物明鉴,无所逃形了。《淮南子•原道》:“夫镜水之与形接也,不设智故(智巧)而方圆曲直能逃也。”晋陆云《答大将军祭酒顾令文》:“心犹水鉴,函景内照。”(《陆士龙集三》)宋苏轼《次韵僧潜见赠》:“道人胸中水镜清,万象起灭无逃形。”
以水镜为心镜,照物照人易,人们日常之中时时处处就都做着这样的功夫,察照着物换星移和别人的一言一动;以水镜为人镜,以人心之镜反照自己难,古语“人贵有自知之明”之贵,正为此也。为此《尚书•酒诰》特别提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墨子•非攻中》跟着也说:“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于凶。”前者说的是为政,后者说的是为人。
就为人而言,中国历史上,魏晋名士严于品评人物,互相砥砺,人镜自照,做得最好。《世说新语》记:“卫伯玉(卫瓘)为尚书令,见乐广与中朝名士谈议,奇之……命子弟造之,曰:‘此人,人之水镜也,见之若披云雾,睹青天。’”卫尚书的赞语,既赞了乐广之清明,尤显尚书自己之在他人之清明中自照自己之难能。诸如此例多不胜举,显示出那个时代的士人们因自我要求奇高而极乐于以他人为镜纠正自身不足之一代风尚。
就为政而言,中国帝王,代天行治,天威至重,能以人为镜返躬自照者稀,能较好做到这一点、且得到历史公认的,当就数唐太宗李世民了。他为政乐于听从臣下意见,尽量做到魏征所谓“兼听则明”,不论什么样意见,正的反的,软的硬的,他都耐心去听,以为说的对他就采纳。他把最直言的魏征比作自己的一面镜子,魏征死,太宗登西楼望哭尽哀,谓侍臣曰:“人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见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魏征没,朕亡一镜矣!”(《新唐书•魏征传》)
109、清以立志,宽和临人
至清者水,以水为镜,法水之清,清洁做人,历来为中国文化首先对文化人提出的要求。
清则贵。无论在朝在野,一清即贵,价值全在于此;相反,则不入于士类,为人所不齿。晋陆机《答张然》诗有谓:“余固水乡客,揔辔临清渊。”(《陆士衡集五》)含蓄点明,他以清自负的高情远志。以宝为宝。陆机自负得对,自洁自清,对于自身怎么严格要求都不嫌过。
至于对人,尽可以温厚一些,不求全责备,明察而不苛求,显示中国文化以水为镜,既求清又保和的博大。清以立则,和以事众,二者同时兼顾。这便是中国文化著名的“水至清则无鱼”的思想。可不要以为这句人人耳熟能详的话只不过是流传于民间的什么格言警句,不是的,它正式地记在规范人的行为的礼书中——《大戴礼•子张问入官》:“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徒。”《孔子家语》中同语记载。
由此推而广之,由为人推及为政,自然就有了为政要求宽简的思想,以善道待民。《后汉书•班超传》记,班超在西域三十一年,惨淡经营,将西域建为汉朝的属地,临老返回洛阳,朝廷任命一位名叫任尚的人前往西域接替班超的职任,任尚临行向班超请教,班超告诫他说,塞外之治,难养易败,“今君性严急,水清无大鱼,察政不得下和,宜荡佚简易,宽小过,总大纲而已。”任尚听了,心里老大不服,私下对人说,“我以班君当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上任后,任尚我行我素,不数年间,西域叛乱频发,局面一塌糊涂。任尚本人由此得罪,被召回洛阳。
110、火治易,水治难,宽猛相济
宽以和众,却又不是愈宽愈和愈好,而要宽严相济。无宽不显严,无严也不彰宽之难能可贵,使人谨慎、珍惜。这一点,又是要取法于水。春秋时,子产为郑国相,郑国治理得井井有条,内安外服。后来,子产年老有病,临死前向大叔交待后事,说:“我死,子必为政。惟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而大叔性情温厚,子产告诫他的话他不能实行,为政一任以宽,结果导致民心放恣,多为盗贼。大叔不得已,只好狠下心来派兵去清剿,反而杀了很多人。大叔后悔说:“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左传•昭二十年》)这一段史实,后来孔子予以总结,提出他的为政观,这样说:“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以是和。”(《论语》)孔子赞扬子产,说他做到了“其养民以惠,其使民也义”,是仁人也。
这样的取法于水火、宽猛相济的政术,后来不折不扣为诸葛亮所领会、贯彻。初入蜀中,诸葛亮佐刘备治蜀,用法颇峻,人多有怨叹者。法政于是谏曰:“昔高祖入关,约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据一州,初有其国,未垂惠抚;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愿缓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无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济。刘璋闇弱,自(刘)焉以来,有累世之恩,文法羁縻,互相奉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蜀土人士,专权自恣,君臣之道,渐以陵替。宠之以位,位极则残;顺之以恩,恩竭则慢。所以致敝,实由于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则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则知荣。恩荣并济,上下有节。为治之要,于斯而著矣。”(《三国志•蜀志》本传)将郑子产以水为镜、宽威相济的施治理念做了透彻说明,以此为纲治蜀,果然大见成效,为后世垂范,成为经典。至今成都诸葛亮祠中悬一副对联:“能攻心则反侧自消,从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对联为清光绪间四川监察使赵藩所撰,上联说的是诸葛亮平南事,下联讲诸葛亮治蜀事,洵为名联。
111、以民为镜
无论宽严,均出于养民保民,而非纯乎一种“机心”运用,一种智巧。在此“宽猛相济”的政治技术的背后,是极为深厚的“民本”文化为其核心支撑,“民本”为一切政治的出发点和归宿,舍此,政治技术运用得愈好而愈成为一种阴谋,不特不值得赞颂,反而应当受到诅咒。
为此,以水为镜,在治国的实践中,也便具体化为“以民为镜”。民心即天心。民不特为浮起统治者宝舟之水,亦且为映照统治者一切施政行为之巨镜之水,纤毫毕照,幽隐无欺。这一点,在中国传统政治宝典《尚书•酒诰》中早有明训:“人无于水监(鉴),当于民监。”欺民、欺水、欺天,可欺人于一时,不可欺人于一世,一定不会有好结果的。
《隋书•赵轨传》记:赵轨为官清廉,任齐州别驾,在州四年,考绩连最。被征入朝,当地父老挥泪相送,说:“别驾在官,水火不与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壶酒相送。请酌一杯水奉饯!”吁!清清一杯水中,照见赵别驾内心多少高贵!照见中国传统文化那深不见底的高贵内蕴,其中那千岁不老之超级生命力难道是凭空说的?
112、化:浴治为本,洗心为上
儒家文化虽然吸收了法家的法术治国思想,以为实际施政行政之有效手段,但整体来说,法在儒学系统中并不占有至上位置,也不过仅仅就是手段而已。在儒学系统中占据至上位置的仍然是道德。道德治国,无论在儒学其学理系统内部,还是在实际的传统中国,从来都既是一种崇高的治世理想,又是一种从宏观到微观实际运用的主要治世方式。即使动用到法,也一定是在道德的笼罩之下运行,最终目的旨在达成于德。
什么是道德治国呢?一句话,就是用道德教化民众,提高民众的道德水平,最终达成广大民众的道德自觉,进到道德自律,从而实现统治者“无为而治”的最高理想。——这就是“化”,荀子水体九德之一之所谓“善化”。那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变化,一种并不需要伤筋动骨而可达致脱胎换骨的变化。就像物从水中走过一遭以后,无声无息,自然而然,污渍得到清洗,而焕然出新,鲜洁芬芳。德法自然:倘若人类在自我教化过程中,也能仿此而收到如此美效,岂不善哉?
于是,自然淘洗,人文化为中国传统文化中道德教化的一种“洗涤文化”,而被泛化延伸到了治国理民的实际操持的实践之中,自然的洗物成洁,化作了人文的洗心达德。
《易经•系辞上》:“六爻之义易以贡,圣人以此洗心,退藏于密。”疏:“行善得吉,行恶遇凶。是荡其恶心也。”
晋潘尼《释奠颂》:“希道慕业,洗心革志。”(出《晋书•潘岳传》附)
《晋书•张天锡传》:“临清流则贵廉洁之行。”
这不光是一种道德号召,朝廷吏治并以此为一项实际任务,布置给各级官员,让他们实际去做。如南北朝时北周皇帝就有诏这样说:“凡诸牧守令长,宜洗心革志,上承朝旨,下宣教化。”(《周书•苏绰传》)
孔子弟子曾皙当年报给老师自己的志向:“阳春三月,春服既成……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论语•先进》)也被引伸,而成为追求高尚情操的一种高志。
一洗成德。“浴德”一词遂成为修养德性的一个专门说法,《礼•儒行》:“儒有澡身而浴德,陈言而伏,静而正之。”疏:“浴德,谓沐浴于德,以德自清也。”
道德,不特成为人追求的崇高目标,道德本身就成为一种最佳的心灵洗涤剂。
顺带指出:儒家以外,道教、佛教,也都格外崇尚“清洁”,将其作为教义的一项基本信条,认为洁是神的内在属性,神性即洁,不洁即非神甚至反神。修行,就是从内到外都做到洁净:于外,二教均有“斋戒沐浴”的仪式讲究,佛教更有“浴佛节”的经典传统节庆;于内,则要求内心的纯洁,不受污染,以善涤心,修善德,结善缘,成善果。道教理论家葛洪《抱朴子•用刑》有谓:“化上而兴善者,必若靡草之逐惊风;洗心而革面者,必若清波之涤轻尘。”
儒教力主洗涤求洁。洁之为德,洗之为务,俨若成为儒学治国的一项日常要务,成为文化的主要担荷者士大夫的必修功课。为达到此崇高目标,士君子必时时自勉,无论顺境或逆境,都不骄不馁,以弘道济民、自洁洁世为自己最高使命,任重而道远,永不停歇。
113、志:炼志如水,水滴石穿
道家(并道教)佛家在野,从来主要以德善化人济世为主务。儒家在朝,儒学为官学,儒士做官为宦,以治业为主务,修德、匡君、牧民均其治业也。
故此,士人们除经历人世间一般的酸甜苦辣,还要经受官场特有的风霜雨雪。二者合在一起,注定士人们其荣耀与苦辛并存,要经历格外多的磨砺,因而要求他们必得有格外坚强的意志,承受格外重的考验。
他们的先师孔子,似乎早已预见到了这一点,早就预先教导他后世的弟子们,务必艰苦炼志,“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论语•子罕》)考验过后,方显本色。又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同上)连匹夫匹妇都做得到的,士君子志士仁人更没得说!
怎么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知者不惑,仁者不忧,勇者不惧。”(同上)只要内心里真的怀有一颗仁心,将仁立为自己立己立人之终极目标,那么有杀身以成仁,而无全身以害义,就一切都不在话下了。
心中有仁,其余一切杂质污物均得涤荡之,清洗之。这仁,成为一种无比强大的内在精神力量,一种孟子所说的“浩然之气”,既充盈于人心,复浩荡于天地之间。于是而,“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孟子》)那立地通天、顶天立地之丈夫之志,就巍然立于天地之间了,一如江河水东流,百折千回,不改其志。水之志,大丈夫之志,此殆即荀子所谓水之九德其最后一德——水志乎!
志,不仅是一种显现于个体人格身上的力量,亦且显现为一种群体文化的力量——历史的力量!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历数千年不改道,一气贯穿下来,直迄而今,那难道不是一种可称为历史特有的意志力量吗?人说历史的长河,文化的长河,在世界历史范围内,也只有中国文化才真的就如同中国的黄河、长江那样,一路流淌下来,而留出如此清晰、完整的连续性轨迹吧。
114、道法自然,德法自然
荀子的水九德说,到了汉代,经儒学大师董仲舒之手,稍作修改,被全面继承下来,推广出去。董作《山川颂》述山川之德,前半颂山,后半颂水。其经过修改后的水之新九德分别为:“既似力者”,“既似持平者”、“既似察者”、“既似知者”、“既似知命者”、“既似善化者”、“既似勇者”、“既似武者”、“既似有德者”。钱钟书先生总结这一段说:道家每言“道法自然”,此则儒家“德法自然”也。(见《管锥篇》第三册)先生慧眼特识,一语道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两支主干其深层内蕴和精神主脉。
115、女人,性争夺的对象
传统中国社会的政治乃至道德,既以水为其智变通转之内在神理,因而也注定将与“女人”的关系纠结不清;其政治文化系统的实际运转,或隐或显,总与女人相关联。
这是不奇怪的,从文化分类学讲,传统文化将女人与水划分为同一类,都归属于阴。从实际历史讲,水为万物生命之源泉,女人为人类生命之源泉;而历史以此生命之泉为中心予以组织、展开,岂不是很自然的吗?
人类历史,自从母系社会转入父系社会,女人失去了对社会的支配权以来,她们便成了社会的一个活的物项,确切地讲,是宝贵稀有之物项。既而她们成为了被争夺的对象,既成为一个社会群体内部争夺的对象,又成为不同族群乃至民族间争夺的对象。就后者而言,当年希腊人与特洛伊人那场为争夺美女海伦所进行的十年浩战,就是最典型的例子。至于有者,则在一个社会内部,每时每刻都在进行,无法胜数了:楚文王灭息国后立即将息夫人占为己有;曹操灭袁绍,曹操儿子曹丕立即冲进袁府将袁绍次子袁熙之妻甄氏纳为己妾;宋灭后蜀,赵匡胤将蜀主孟昶妃子花蕊夫人收入后宫,等等,是其荦荦大者;民间生活中,《金瓶梅》西门庆之夺潘金莲,《红楼梦》薛潘之夺占香菱,等等,多如牛毛。
116、冰肌玉骨,朝云暮雨
总起来讲,水之与女人的关系,约有这样三个要点:
第一,水女同态,水态即女态:其柔,其爽,其盈盈脉脉,婀娜多姿,在中国文化看来,皆神理相通,韵致如一。于是而有苏东坡的著名诗句这样说:“欲将西湖比西子,浓妆淡抹总相宜。”有曹雪芹的著名文学比喻这样说:“女人是水做的骨肉,男人是泥做的骨肉。”一说立即得到所有人的响应,成为经典。那是说到人们的心里去了。
第二,水女同性,同为周流不居,徙移不定。宋玉笔下的巫山神女,自称“朝为行云,暮为行雨”。明清人的戏曲小说,则更干脆以“水性杨花”相比喻,以况女人之朝张暮李属主不定,如李玉《一捧雪》这样唱道:“杨花水性随风折,怎顾得生离死别?喜孜孜早觅个俏冤家,把个姻缘再来接。”到最后,由外而内,索性把这种女人的外在归属的飘忽不定,说成是女人的内在心性,仿佛这些水为肌骨的女儿们乃天生尤物,用情喜变,水流百家转,而倒与社会的男人们及其所主宰的文化了无关系似的。
117、红颜祸水
由是,如此一群冰肌玉骨、水灵鲜洁,如此被强大男人们所渴念、“恨不能一口水吞了去”(明清小说用语)的女人们,既然现实中如流水一样极具可变的周流性,朝可属秦暮可属楚,于是骚动不安的男人们按捺不住开始动起手来:争吵,抢夺,阴谋阳谋,直至斗杀、战争,为了占有女人,尤其是那些美丽稀有的好女人。拼杀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小到头破血流,家破人亡,大到战火绵延,亡国灭族,层出不穷。
事后,文化对此惨烈异常的争夺进行反思,反而归咎于女人:希腊人经过十年鏖战,十死八伤,最后灭掉特洛伊,带着海伦回国,国人一睹美人真容后,不约而同齐声赞道:啧啧!为了这样的女人打这样一场战争,值!但接着就说,她可真的是美得有些可怕,我们还是离她远点吧。在中国,既对女人特别的贪得无厌,恨不能后宫里把全天下所有美人一口袋都装了去,复又对亡家亡国的后果特别怕得要命,在这种特别矛盾的心情里,于是而文过饰非,好事自己占,恶果迁罪于女人,认为——
第三,水女同害,认为女人是“祸水”。好看的女人尤其是不祥之物:西汉成帝宠爱美人赵飞燕、赵合德姐妹,有博士名淖方成者适在宫中,震惊于赵合德之美,当着成帝的面当下唾曰:“此祸水也,灭火必矣!”(出旧题汉伶玄著《飞燕外传》)汉朝号称以火德王天下,灭火者,灭汉之谓。实际,成帝朝承平无事,上下相安。而成帝本人,善修仪容,尊严若神——班固《汉书•成帝纪》如是说。但班固紧接着转笔这样写道:“然湛于酒色,赵氏乱内,外家擅朝……哀、平短祚,莽遂篡位,其威福所由来者渐矣。”认为正是由于成帝宠女色,而开外戚专权的先河,长期累积,终于权移于外,导致西汉末哀平间的王莽篡汉。
顺便说到,在中国文化中,女人与酒总是同提并举,称为“酒色”。有意思的是,女人被称为“祸水”,而酒则被称为“祸泉”。宋陶榖《清异录》六一《酒浆》:“酌于杯,注于肠……性昏志乱,胆胀身狂。平日不敢为者为之,平日不敢言者言之。言腾烟焰,事堕阱机,是岂圣人贤人乎?一言蔽之,曰祸泉而已。”
而中国历史,也就开出一列长长的酒色乱国亡国的详细清单:商纣王宠妲己,周幽王宠褒姒,吴王夫差宠西施,唐明皇宠杨玉环……与此相对应的美女们则有,妲己,褒姒,西施,杨玉环……愈是美得狠,愈是祸得深!
女人祸国,客观而论,不能说全无道理,不能因为今天我们尊重女,便去刻意回避这个事实。道理很简单:作为个体的人来说,性爱自为生命的内在规定性,愈是爱得深爱得烈,生命愈是在性爱中得到最大张杨,愈合于生命之本性。这是不成问题的。古人也充分承认,说:“食色,性也。”但是对于国家来说,对于国家官员、尤其是作为国家象征之皇上来说,就不能这样说了:当他把他的全部身心都投入到天昏地暗的性爱之中的时候,当他不可能不借用手中的权力去为其天昏地暗的性爱更煽起腾天烈焰的时候,国家于是也便失去其独立的品格,而成为他作为生物个体其一己之性爱的助燃剂,国事于是也便成为国王一己之性事,这时,色性——又如何能不说是一种可怕的祸害?皇上、官员等掌握公权国器的他们倒是爱得足心足意了,国家怎么办?百姓怎么办?像南朝陈后主那样,“城外韩擒虎,楼头张丽华”——城外隋军已然随大将韩擒虎汹涌而来准备爬城,而后主先生却依然与爱姬丽华女士在楼头爱得欲仙谷死,此种爱,那不是祸又是什么!
女人与水,当其施用于不恰当之场合,女人流荡于朝堂公廨,大水浩荡于田舍家园的时候,二者就都成了祸水,是该到来一场大禹治水的时候了。
118、国家,不是献给女人的一朵鲜花
不过,不可以不明白的是,这整个事情,主要责任当归男人来负,因为,他是主动者,他掌局,事前的一切都是他预先安排好的。女人是被动的一方,她不过是别无选择地进入男人的预定安排,在进入之后借势玩一把她有限的小技术而已。虽说是小技术,却时常变生出出人意料的大后果,因为她借势和玩耍的对象是皇上,是整个国家力量的浓缩,就在她玩皇上的时候,牵一发而动全身,她实际已将国家玩弄于她的股掌之上,石榴裙下。为此,传统中国对于女人,总是怀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传统社会其所以压迫妇女到了变态的地步正是这种恐惧的结果,总是保持高度的警惕,一再一再申述不休:女人与太监,不许干政!
但这是不可能的。造化造就:男人天生爱女人,超过对其他一切宝物的爱,没有办法抗拒。爱到极处,既要绝对的占有,又情不自禁绝对地奉献,其中包括权力和国家。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不惜“烽火戏诸侯”,拿国家做了情戏的道具,哪怕一笑之间,江山大堤崩塌,也顾不得了。
性爱之为物,在人类所有情感中,的确是最为特殊的一种,特殊就特殊在:其他所有感情,总或轻或重带有某种自私的性质,惟独爱情,互相媚悦,绝对无私,它是以博取对方的欢心为自己欢心之条件。那么怎么样博取对方欢心呢?那就是,毫不吝惜地各自拿出自己所拥有最好的东西,作为礼物献给对方:女人拿出自己的美貌,男人拿出自己的力量——身体的力量以及身体力量的延长——权力和财富的力量。女人把自己作为世界献给男人,男人把世界作为自己献给女人。
但世界只有一个,它归世界所有人所有,不能听任世界中某个男人整个端走献给他的女人。于是文化定出规矩,国家与个人实行某种程度的分离,不允许国家事务与个人情感搅在一起,也便成为世界绝大多数民族政治文化的通则。
可是,这通行的原则在实际执行中,中国与西方其具体执行方式却又大有不同——
西方中世纪,有强大的教会,而将天下所有人的爱情与婚姻的事务,统统视为是上帝的事务,神的事务,一并收归自己掌管,根据教义,实行一夫一妻制,不准离婚,国王也不例外。弄得国王苦不堪言,只好也如乡下汉一样偷偷摸摸去找个把情妇去混混,以遣寂寞。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性爱生活,于是被大大地简化,而较少干扰国家的政治生活;尤其在不爱妻子爱情妇的情况下,更不能公然以情妇的名义对国家开说,说要怎样怎样。并且,作为国王,在上有强大教会的精神箝制,在下有强大贵族的实力牵制,国王夹在中间,力量实在有限,即使他激情汹涌,爱得发颠发狂,也只能在一个多半是私人的范围内展开,而无法牵动整个国家,把国家作了他的性事的婚床予以尽情发泄。他当然是不尽兴得很,但也只有忍着。
而在中国,却作别一种解决。中国文化信奉物极必反,盈而后亏的智慧为儒道两家同信,他们认为,“食多伤人”,“香浓失味”,“花多不艳”,“糖多不甜”。为此中国传统文化形成一套崇尚淡雅的美学文化意识,无论什么,处人也罢做事也罢,总以做到八成、不做满做足为要,要含蓄,要内敛,从而既使人得以体会体味那难得的最高境界的美,又得保持长久,余味无穷。而女人的装束也要大遮小露,给男人留下足够大遐想的美学空间,坚决拒绝一览无余,了无余味。
有趣的是,这样一种基于哲学智慧的高级美学文化,它用在政治上,竟形成为一种古怪的对付专制君王的手段:戗害君王的味觉,使之对女人失去有效审美感觉,从而失去对女人的兴趣。不是说怕君王把自己的情事与国家的国事搅在一起,影响国家大政吗?那么好,传统文化不是像西方人那样,借用教会神典对国王进行性事的限制;而是相反,文化设计出一种“厌足法”:就让王放开了去玩女人,十倍百倍千倍超出常人地去玩,后宫塞满了女人,成千上万,就让王去玩,吃吃吃吃,直到食多伤心,到你厌足到见了女人就想吐的地步,看你还再对女人有兴趣不!人产生渴念,常是因为匮乏的缘故。君王既然对女人已然十二分厌足,再不存在一丁点儿的渴念,那么这时我主万岁他就该不用再为了女人的事分心,在朝堂上可以全心全意就国论国,专心处理国事了。
请不要误会:以为以上我是在说,仿佛造成传统中国的一夫多妻制,是传统中国文化的一种有意的“谋划设计”,仿佛是个阴谋。不是这样的。谋划是谋划不来的。那不是一种设计,而是一种“机制”,一种文化机制,用以解决传统中国所特有的“超级集权君主”条件下,如何实现国事与国王个人情事有效分离这样一个难题。
当然,这决不是一个好的解决办法,第一,侮辱女性,不合人性;第二,也难得做到万无一失,常出毛病,前述商纣王、周幽王便是好例。
但是,这无法由人选择,因为它不是由人有意设计。文化只是在盲目中,缓慢地一点一点地修正完善其机制,以勉强应付一个又一个历史难题。正如大堤当水,经常决堤出事,却谁也不能说:为什么不去建一个万年不坏的金刚之堤,那岂不更好?自然物种的进化是靠了“自然选择”的自然规律来实现的,文化的进化有没有一只上帝之手——自然选择——在暗中予以拨动?我感觉一定是有的。
119、十大美女,十个历史危机时期的标志
中国文化的大堤亦如黄河上所建“金堤”一样,堤的耐力与水的压力总处于一种平衡状态。此时,波平堤静,二力和睦相处,看上去仿佛一对恩爱夫妻,谁也想不到会有决裂的那一天。可惜的是,水续续而来,总是新的,日日年轻。而堤一天老一天,走向衰迈。总有一天,老夫少妻实在不般配了,少妻不想再受束缚,决堤而去不回头。于是保婚人手忙脚乱,赶紧抢修,将私奔的媳妇给捉回来,重新捆绑,新堤新水成新夫妻。王朝的运转,兴废隆替,亦是如此。王朝的规矩就是那堤,王朝中女性的力量就是那水。于是而中国历史上每隔几百年,也就要“产生”出一个超凡出众的绝世“美女”来。这真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
现在你大概已经明白我要说什么了:传统中国历来号称有什么什么几大“美女”,什么意思?难道说这是一种“生物或天体现象”——仿佛美女真应着天上某颗神星的运行周期,应运而生的吗?当然不是。这是一种不折不扣的文化现象——确切地说,一种传统中国政治文化特有的现象。每一个“美女”的诞生,她不是对应着天上某恒星运转所至某个点位,而是:恰好正对应着中国历史的一个“危机时刻”,妲己,褒姒,西施,赵飞燕,王昭君,貂蝉,杨玉环,李师师,陈圆圆,赛金花——以上十位“国色”正分别对应了中国历史上十个王朝所发生的十次危机。真是奇妙得很啊!
该怎么样来解读这种奇而又奇的“历史现象”呢?有两种解读的方法:一种是,美女的确不祥,是祸水,是她们引致王朝的覆灭,可谓是国色覆国,邑色覆族,乡色覆家。所谓一笑倾人城,再笑倾人国。倾者,覆也。如果说美人奇货,不可避免要引来恶势力的觊觎,最后造成国破家亡的奇祸,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有道理,武大郎家当年就是这么灭门的。如果说,美人格外招人爱怜,她凭其美色之力量完全控制了男人,任性胡来,乱了国政家政,最后造致国破家亡,从这个意义讲,也有道理,周幽王当年亡国身死就是这样的。
但还有另一种解读的方法,那就是,把国破家亡这个事情的因果给它倒过来:国破家亡这个事情本不是由美人造成的,或者说即使真跟她有些关系,但关系并不大;事情的真相是:国破家亡如此大的事件,那是一定得有人出面来承担责任的,才好向世人、也向千秋万代的历史有个交待,于是乎,美女被选出来,就由她来承担此罪名,省事,又好做后来者一个警示,一举两得。这么解读更有道理,因为,男权社会的历史中,再厉害的女人其力量毕竟有限,再说,那男人皇上难道真的是司马衷式的傻子呆子吗?更何况